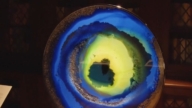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5月06日讯】
1、回忆清明上坟的景象
这条路两旁种满了的芒果树,在三月节里,结了青绿果实,陆陆续续来上坟的人,迤逦至应公庙前。午后阳光的淫威在树叶间穿梭,瑞弟穿着拖鞋,掮着锄头走在前头,锄柄上挂着的畚箕在背后晃荡着。
庙前已聚集了一簇簇人群,纷沓的谈话声夹杂着卖冰水的铃铛,使上坟期间的庙前形成的小市集更显得热闹。我提着白色帆布袋子,袋里装了水壶、镰刀、火柴,将袋子倚在庙柱上,抬起手臂用袖子在额上擦了擦汗。瑞弟那副锄头、畚箕还高高挂在肩上,他站在金炉旁芒菓树下的金银纸摊前,跟伙计喧谈着,然后,走了过来,把手上金银纸放进帆布袋里。
我们往庙后的小路走,前面是一座小山崙,坡上错落着大大小小坟头,只让出一条小径蜿蜒至山顶。父亲的坟墓在后山,还得越过这山崙,野草不时擦过腰际,碰到扫完坟的人,还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瑞弟一声不响地扛着锄头往坡上爬,把我抛得远远的,只能看到他的背脊。
2、想念少年日子的酸甜苦涩
“阿瑞啊,得小心。”我仿佛听到这声音在山坡回响。那时,我们还是毛头小子,看着瑞弟的身躯吊挂在龙眼树枝上,我几乎吓得手脚发软。
“阿瑞,你得小心。”我攀伏在一个大人高的墙上,吆喝声渐渐小了,最后只有自己能听见。我必须观察墙里的动静,还得接住瑞弟从树上抛下来的一串串龙眼,而最怕的是,那只不响不叫的老黄狗,还好,想着袋里圆滚圆滚的龙眼时,手脚发软的程度就好了些。
此刻,院子里死寂无声,管园的老伯大概睡午睡去了,偏也看不到老黄狗的踪影,心里像脚踏车失了刹车,没了准儿。我瞄瞄树上的瑞弟,粗枝上的龙眼都让他摘光了,现在正往枝尾爬,可那根枝条上下晃荡着,几乎载不住瑞弟的身体了,我抓紧袋口,把院子扫视一圈,忽然,角门侧边一个影子闪过,又不见了,我压低声音向上喊着︰“阿瑞,快下来,快下来。”
瑞弟转过头瞧了我一眼,一阵风扫过他衣襟,树叶毕毕剥剥响着,他松开右手就要攀下来,刹时,整根树枝“叭”的一声,断裂开来。我还来不及看瑞弟落下来的惨状,一个影子已从角门后侧闪电似的蹿了出来,“老黄狗!”我吓得只能吐出这三个字时,瑞弟已不偏不倚地摔在老黄身上,于此同时,我抓起一把龙眼照准老黄狠命掷去,老黄抬起前脚,尖叫了两声,说时迟那时快,瑞弟已奔上来,抓着我的小腿,跃上了围墙。
那天下午,我们躲在城顶街水井边,喘过了气后,把袋里的龙眼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天亮时,瑞弟躺在床上呻吟着,我拉开他裤子,屁股已红肿了一大块。
3、越过那坪山崙
我们奔上父亲坟头,一年没来,坟上野草丛生,已有半个人高了。傲慢的猪母苓草,肆意地在土里钻进钻出,一朵小黄花孤立香炉里,随风飘荡。父亲墓碑字迹已褪了颜色,只剩凹陷的刻痕,我把撮撮野草摘掉了。
瑞弟挥起镰刀,刷刷地一会工夫,身旁野草已堆成小山。瑞弟弓着腰割草的身影,跟小时候可真是一模一样,只是比以前壮多了,不像以前瘦骨嶙峋的。
记得一个夜里,瑞弟把我从床上叫醒:“阿和,快点,下雨了。”我醒过来时,才发现裤子都被雨水打湿了。旁边铺位空空的,早早出去工作的母亲还没回来。
“快点啊。”瑞弟把脸盆递给我,这时我才听到外面凄厉的雨声,及雨水滴落水桶、瓶瓶罐罐,叮叮咚咚的响声,清晰结实。窗户噗噗震动着,我从床上跪行过去,把窗户锁紧了。瑞弟还在忙着搬桌椅、衣服,在昏黄灯光下,我看到饭桌下已积了一洼水。雨还下着,我想寻找窗前那棵老茄苳的影子,只是漆黑一片。
最后瑞弟气急败坏的缩着头爬过来,我们靠着墙壁坐在床上,瑞弟头髪湿了,我抓了条破旧汗衫替他擦头上的雨水,他一手把我推开,不说话。我们坐在床上,听着屋里的水滴声,听着窗外的雨声,等待雨停。
第二天,雨停了,醒来时,瑞弟正睡得酣熟,我们小肚子都盖着老绵袄,屋里静静的,母亲又出去工作了。
4、走进巷里的人是瑞弟
那时,我小学四年级,在一个苦苓树影洒满小土巷的傍晚,我与几个孩子在树下玩玻璃珠,那可是玩真的,眼看着一个个玻璃珠被我打入洞里,阿永三个人的眼睛也鼓得像玻璃珠,最后我的两个裤袋都装满了玻璃珠,两腿一动,玻璃珠就“晶晶”的响着。阳光黯了下来,我拍拍手上灰土:“回家吃饭了,明天再玩。”
三个人站了起来,看着我的裤袋,阿永面无表情歪着脑袋,伸出手掌:“拿出来。”我握紧裤袋,阿永逼近来,抓住我的手臂,我要把他推开时,小腿已被踢了一脚,脚一软,我跪到地上,马上有人趴了上来。我大喊:“有种的,一个对一个。”
“全部拿出来!”阿永的拳头扎实地落在我小肚上,我叫了一声,随着两手松开,玻璃珠滚了一地,两个人上来抱着我,一个捡拾地上的玻璃珠,我越挣扎,他们越死命抱紧我,那时,真希望有人经过这里——赫,真有人来了。
“他们抢我的玻璃珠!”于是他们放下我,往巷口冲出去。那个人站在巷口,手里握着木棒,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棒,挡住他们。我只顾嘶声喊着:“他们抢我的玻璃珠。”那人背着阳光走进巷子,几乎看不清脸孔,他把木棒横在胸前,三个小子把玻璃珠抛在地上,一个个跑掉了。
我走过去检拾满地的玻璃珠时,才看清楚,原来是瑞弟。
5、锣鼓喧阗 布袋戏上演了
那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清明一到,整条城顶街两旁矮屋子,一家挨一家拥挤着,到了妈祖生辰那天,庙前搭盖起来的布袋戏棚,挺拔着与午后艳阳打起交道。
戏刚开锣,瑞弟就拉着我攀上戏棚后台,那个敲着小硬鼓的老艺师,眯着眼珠斜视我们,另一头棚柱边也蟠踞了一些人,望着敲锣打鼓的艺师。瑞弟干脆坐在棚板上,两手抱着膝盖,下颏抵在膝头上:“这里有帆布挡着太阳,风从榕树那边吹过来,没人知道这里最凉快。”戏台左斜角那棵老榕树上,攀附着几个人,摇摇晃晃地吊在半空中。
一脚木屐猛踹在棚板上的震天巨响,吓了我们一跳,等我们收住神时,一阵锣鼓声急促的跟了上来,那个敲小硬鼓的,卖力打着,场面就热闹了起来,两个布袋戏偶在戏台上飞来飞去,那叫“哪吒”的小子连连打了胜仗,台前惊呼连着掌声。
卖腌番石榴的老妇人叫嚷了两声,我跟瑞弟都掉过头来,一个个翠绿沾着糖粒的削皮番石榴,在老妇摊上木盆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戏台上,摇晃出一个白面书生,小锣小鼓有一搭没一搭地伴着。那个老艺师敲着小硬鼓,欲困欲睡的样子,一声咳嗽后,瞧了我们一会,招呼我们过去。我们迟疑着,他又向我们招呼,瑞弟就走了过去。
他把一根长长的鼓箸交到瑞弟手里,教瑞弟跟着节拍打,然后咬着瑞弟耳朵咕哝了两声,攀下棚台去了。瑞弟挺着胸膛敲击起来,头也跟着一下下点着。
半碗茶工夫,那艺师回来了,瑞弟把鼓箸还给他时,他摸摸瑞弟的头,咧开嘴笑了。这时,太阳已斜过庙檐燕尾去了,庙口两只石狮子兀自张着嘴巴。
回家路上,瑞弟的两只食指还在上上下下敲打着,嘴里起咚起咚碎念着。
我升上初四那年,瑞弟又转到汽车修理厂当学徒。有一天放学回家,瑞弟看见我就叫嚷起来:“阿和,你的大字得第一名了。”那幅我临摹的书法作品上,已印上瑞弟两个污黑的手指印,我从他手上抢过来,另一手揍上他下巴,他一个踉跄,脑袋跌撞床角上,一阵乒乓响。母亲从房里跑出来:“你打弟弟了!”瑞弟抱着头,苦着脸说:“我自己跌倒的。”那天夜里,躺在床上,瑞弟跟我说:“我以后不干黑手学徒的工作了。”
如今我才了解,瑞弟为了护我,把委屈都吞进肚子里了。
6、等待纯真归来 迎接新纪元
“阿和,快来哦。”瑞弟站在山崙顶,把畚箕举在头上向我招呼,我小跑着赶了上去。
山顶上,瑞弟正抓着脱下来的衬衫往额上擦汗,两只断了耳的拖鞋抛在地上。我喘了口气:“叫你穿布鞋,偏贪凉快,这趟有你受的。”瑞弟两只呆呆的脚ㄚ子贴着黄土地面,他嘻嘻笑着,太阳高高挂在头上,专门对付我们似的,把影子拖得长长的。我问瑞弟:“最近生意好吗?”他走在前面,头也不回,手掌扬上天空:“不错,上个月订了新车,裕隆一千二,再打拼点,明年就可以买房子了。”
瑞弟小学毕业,就坚持不读书:“我要赚钱,赚钱。”那时,母亲拗不过他,气得扒在门柱上哭,瑞弟抬起脚用木屐“苦苦”的踢着门槛边的大铝盆:“阿母无暝无日洗衣服,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厝边头尾说你手指都磨破了。”母亲蹲了下来,把头埋在膝盖上,脖子不停颤动着,却听不见哭声。后来母亲还是斗不过瑞弟,让他到大街上石头师的糕饼铺当学徒。记得那年中秋节,我们就不缺月饼吃了,瑞弟亲自做的。
我们给父亲上了香,烧了银纸后,四周坟头孤孤寂寂的,只剩几个人走动。我们坐在黄土堆上休息,瑞弟眯眼望着太阳,脖子上灰土都被污水浸湿了。我站了起来,戴上斗笠,望了一眼父亲墓碑周围的缕缕青烟,檀香已烧了一大截。“回去吧。”瑞弟站了起来,拍掉屁股上的黄土。
我们跃上山崙时,山麓的应公庙像个鸡笼,瑞弟扛着锄头畚箕,转过头来:“我到杂货店带两瓶冰啤酒,回去喝两杯吧,让阿母切盘鸡翅膀。”我站在山崙上往城里望去,城顶街上空,放射着片片金色光芒。
在社会紊乱、光明与黑暗交错的十字路口,回首过去淳朴纯真的日子,从少年到成年,不过半个世纪、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此刻、仰望苍穹蓝天,心里充满平静祥和,盈溢无尽光明与希望。@*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