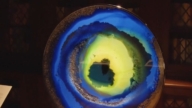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5月06日訊】
1、回憶清明上墳的景象
這條路兩旁種滿了的芒果樹,在三月節裡,結了青綠果實,陸陸續續來上墳的人,迤邐至應公廟前。午後陽光的淫威在樹葉間穿梭,瑞弟穿著拖鞋,掮著鋤頭走在前頭,鋤柄上掛著的畚箕在背後晃蕩著。
廟前已聚集了一簇簇人群,紛沓的談話聲夾雜著賣冰水的鈴鐺,使上墳期間的廟前形成的小市集更顯得熱鬧。我提著白色帆布袋子,袋裡裝了水壺、鐮刀、火柴,將袋子倚在廟柱上,抬起手臂用袖子在額上擦了擦汗。瑞弟那副鋤頭、畚箕還高高掛在肩上,他站在金爐旁芒菓樹下的金銀紙攤前,跟伙計喧談著,然後,走了過來,把手上金銀紙放進帆布袋裡。
我們往廟後的小路走,前面是一座小山崙,坡上錯落著大大小小墳頭,只讓出一條小徑蜿蜒至山頂。父親的墳墓在後山,還得越過這山崙,野草不時擦過腰際,碰到掃完墳的人,還得側著身子才能過去。瑞弟一聲不響地扛著鋤頭往坡上爬,把我拋得遠遠的,只能看到他的背脊。
2、想念少年日子的酸甜苦澀
「阿瑞啊,得小心。」我彷彿聽到這聲音在山坡迴響。那時,我們還是毛頭小子,看著瑞弟的身軀吊掛在龍眼樹枝上,我幾乎嚇得手腳發軟。
「阿瑞,你得小心。」我攀伏在一個大人高的牆上,吆喝聲漸漸小了,最後只有自己能聽見。我必須觀察牆裡的動靜,還得接住瑞弟從樹上拋下來的一串串龍眼,而最怕的是,那隻不響不叫的老黃狗,還好,想著袋裡圓滾圓滾的龍眼時,手腳發軟的程度就好了些。
此刻,院子裡死寂無聲,管園的老伯大概睡午睡去了,偏也看不到老黃狗的蹤影,心裡像腳踏車失了剎車,沒了準兒。我瞄瞄樹上的瑞弟,粗枝上的龍眼都讓他摘光了,現在正往枝尾爬,可那根枝條上下晃蕩著,幾乎載不住瑞弟的身體了,我抓緊袋口,把院子掃視一圈,忽然,角門側邊一個影子閃過,又不見了,我壓低聲音向上喊著︰「阿瑞,快下來,快下來。」
瑞弟轉過頭瞧了我一眼,一陣風掃過他衣襟,樹葉畢畢剝剝響著,他鬆開右手就要攀下來,剎時,整根樹枝「叭」的一聲,斷裂開來。我還來不及看瑞弟落下來的慘狀,一個影子已從角門後側閃電似的躥了出來,「老黃狗!」我嚇得只能吐出這三個字時,瑞弟已不偏不倚地摔在老黃身上,於此同時,我抓起一把龍眼照準老黃狠命擲去,老黃抬起前腳,尖叫了兩聲,說時遲那時快,瑞弟已奔上來,抓著我的小腿,躍上了圍牆。
那天下午,我們躲在城頂街水井邊,喘過了氣後,把袋裡的龍眼吃了個精光。第二天,天亮時,瑞弟躺在床上呻吟著,我拉開他褲子,屁股已紅腫了一大塊。
3、越過那坪山崙
我們奔上父親墳頭,一年沒來,墳上野草叢生,已有半個人高了。傲慢的豬母苓草,肆意地在土裡鑽進鑽出,一朵小黃花孤立香爐裡,隨風飄蕩。父親墓碑字跡已褪了顏色,只剩凹陷的刻痕,我把撮撮野草摘掉了。
瑞弟揮起鎌刀,刷刷地一會工夫,身旁野草已堆成小山。瑞弟弓著腰割草的身影,跟小時候可真是一模一樣,只是比以前壯多了,不像以前瘦骨嶙峋的。
記得一個夜裡,瑞弟把我從床上叫醒:「阿和,快點,下雨了。」我醒過來時,才發現褲子都被雨水打濕了。旁邊鋪位空空的,早早出去工作的母親還沒回來。
「快點啊。」瑞弟把臉盆遞給我,這時我才聽到外面淒厲的雨聲,及雨水滴落水桶、瓶瓶罐罐,叮叮咚咚的響聲,清晰結實。窗戶噗噗震動著,我從床上跪行過去,把窗戶鎖緊了。瑞弟還在忙著搬桌椅、衣服,在昏黃燈光下,我看到飯桌下已積了一窪水。雨還下著,我想尋找窗前那棵老茄苳的影子,只是漆黑一片。
最後瑞弟氣急敗壞的縮著頭爬過來,我們靠著牆壁坐在床上,瑞弟頭髪濕了,我抓了條破舊汗衫替他擦頭上的雨水,他一手把我推開,不說話。我們坐在床上,聽著屋裡的水滴聲,聽著窗外的雨聲,等待雨停。
第二天,雨停了,醒來時,瑞弟正睡得酣熟,我們小肚子都蓋著老綿襖,屋裡靜靜的,母親又出去工作了。
4、走進巷裡的人是瑞弟
那時,我小學四年級,在一個苦苓樹影灑滿小土巷的傍晚,我與幾個孩子在樹下玩玻璃珠,那可是玩真的,眼看著一個個玻璃珠被我打入洞裡,阿永三個人的眼睛也鼓得像玻璃珠,最後我的兩個褲袋都裝滿了玻璃珠,兩腿一動,玻璃珠就「晶晶」的響著。陽光黯了下來,我拍拍手上灰土:「回家吃飯了,明天再玩。」
三個人站了起來,看著我的褲袋,阿永面無表情歪著腦袋,伸出手掌:「拿出來。」我握緊褲袋,阿永逼近來,抓住我的手臂,我要把他推開時,小腿已被踢了一腳,腳一軟,我跪到地上,馬上有人趴了上來。我大喊:「有種的,一個對一個。」
「全部拿出來!」阿永的拳頭紮實地落在我小肚上,我叫了一聲,隨著兩手鬆開,玻璃珠滾了一地,兩個人上來抱著我,一個撿拾地上的玻璃珠,我越掙扎,他們越死命抱緊我,那時,真希望有人經過這裡——赫,真有人來了。
「他們搶我的玻璃珠!」於是他們放下我,往巷口衝出去。那個人站在巷口,手裡握著木棒,一根又長又粗的木棒,擋住他們。我只顧嘶聲喊著:「他們搶我的玻璃珠。」那人背著陽光走進巷子,幾乎看不清臉孔,他把木棒橫在胸前,三個小子把玻璃珠拋在地上,一個個跑掉了。
我走過去檢拾滿地的玻璃珠時,才看清楚,原來是瑞弟。
5、鑼鼓喧闐 布袋戲上演了
那年,夏天來得特別早,清明一到,整條城頂街兩旁矮屋子,一家挨一家擁擠著,到了媽祖生辰那天,廟前搭蓋起來的布袋戲棚,挺拔著與午後豔陽打起交道。
戲剛開鑼,瑞弟就拉著我攀上戲棚後台,那個敲著小硬鼓的老藝師,瞇著眼珠斜視我們,另一頭棚柱邊也蟠踞了一些人,望著敲鑼打鼓的藝師。瑞弟乾脆坐在棚板上,兩手抱著膝蓋,下頦抵在膝頭上:「這裡有帆布擋著太陽,風從榕樹那邊吹過來,沒人知道這裡最涼快。」戲台左斜角那棵老榕樹上,攀附著幾個人,搖搖晃晃地吊在半空中。
一腳木屐猛踹在棚板上的震天巨響,嚇了我們一跳,等我們收住神時,一陣鑼鼓聲急促的跟了上來,那個敲小硬鼓的,賣力打著,場面就熱鬧了起來,兩個布袋戲偶在戲台上飛來飛去,那叫「哪吒」的小子連連打了勝仗,台前驚呼連著掌聲。
賣醃番石榴的老婦人叫嚷了兩聲,我跟瑞弟都掉過頭來,一個個翠綠沾著糖粒的削皮番石榴,在老婦攤上木盆裡,堆成了一座小山。
戲台上,搖晃出一個白面書生,小鑼小鼓有一搭沒一搭地伴著。那個老藝師敲著小硬鼓,欲睏欲睡的樣子,一聲咳嗽後,瞧了我們一會,招呼我們過去。我們遲疑著,他又向我們招呼,瑞弟就走了過去。
他把一根長長的鼓箸交到瑞弟手裡,教瑞弟跟著節拍打,然後咬著瑞弟耳朵咕噥了兩聲,攀下棚台去了。瑞弟挺著胸膛敲擊起來,頭也跟著一下下點著。
半碗茶工夫,那藝師回來了,瑞弟把鼓箸還給他時,他摸摸瑞弟的頭,咧開嘴笑了。這時,太陽已斜過廟簷燕尾去了,廟口兩隻石獅子兀自張著嘴巴。
回家路上,瑞弟的兩隻食指還在上上下下敲打著,嘴裡起咚起咚碎唸著。
我升上初四那年,瑞弟又轉到汽車修理廠當學徒。有一天放學回家,瑞弟看見我就叫嚷起來:「阿和,你的大字得第一名了。」那幅我臨摹的書法作品上,已印上瑞弟兩個汚黑的手指印,我從他手上搶過來,另一手揍上他下巴,他一個踉蹌,腦袋跌撞床角上,一陣乒乓響。母親從房裡跑出來:「你打弟弟了!」瑞弟抱著頭,苦著臉說:「我自己跌倒的。」那天夜裡,躺在床上,瑞弟跟我說:「我以後不幹黑手學徒的工作了。」
如今我才瞭解,瑞弟為了護我,把委屈都吞進肚子裡了。
6、等待純真歸來 迎接新紀元
「阿和,快來哦。」瑞弟站在山崙頂,把畚箕舉在頭上向我招呼,我小跑著趕了上去。
山頂上,瑞弟正抓著脫下來的襯衫往額上擦汗,兩隻斷了耳的拖鞋拋在地上。我喘了口氣:「叫你穿布鞋,偏貪涼快,這趟有你受的。」瑞弟兩隻呆呆的腳ㄚ子貼著黃土地面,他嘻嘻笑著,太陽高高掛在頭上,專門對付我們似的,把影子拖得長長的。我問瑞弟:「最近生意好嗎?」他走在前面,頭也不回,手掌揚上天空:「不錯,上個月訂了新車,裕隆一千二,再打拚點,明年就可以買房子了。」
瑞弟小學畢業,就堅持不讀書:「我要賺錢,賺錢。」那時,母親拗不過他,氣得扒在門柱上哭,瑞弟抬起腳用木屐「苦苦」的踢著門檻邊的大鋁盆:「阿母無暝無日洗衣服,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厝邊頭尾說你手指都磨破了。」母親蹲了下來,把頭埋在膝蓋上,脖子不停顫動著,卻聽不見哭聲。後來母親還是鬥不過瑞弟,讓他到大街上石頭師的糕餅鋪當學徒。記得那年中秋節,我們就不缺月餅吃了,瑞弟親自做的。
我們給父親上了香,燒了銀紙後,四周墳頭孤孤寂寂的,只剩幾個人走動。我們坐在黃土堆上休息,瑞弟瞇眼望著太陽,脖子上灰土都被汙水浸濕了。我站了起來,戴上斗笠,望了一眼父親墓碑周圍的縷縷青煙,檀香已燒了一大截。「回去吧。」瑞弟站了起來,拍掉屁股上的黃土。
我們躍上山崙時,山麓的應公廟像個雞籠,瑞弟扛著鋤頭畚箕,轉過頭來:「我到雜貨店帶兩瓶冰啤酒,回去喝兩杯吧,讓阿母切盤雞翅膀。」我站在山崙上往城裡望去,城頂街上空,放射著片片金色光芒。
在社會紊亂、光明與黑暗交錯的十字路口,回首過去淳樸純真的日子,從少年到成年,不過半個世紀、幾十年,依然歷歷在目,此刻、仰望蒼穹藍天,心裡充滿平靜祥和,盈溢無盡光明與希望。@*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