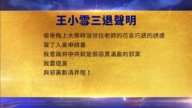【新唐人2017年01月11日讯】按:余文生律师,2014年因涉嫌支持“香港占中”被抓捕,羁押99天期间遭受酷刑。2015年他一度因709事件被抓,后成为王全璋律师的代理律师;2016年8月,其代理身份被强行剥夺,同年,代理大量法轮功案件。本文为专访的下半部分。
(续前篇)
记者:那您现在的日常信息来源是什么?您看电视吗?
余文生:现在的日常信息主要是网络,首先看国内的网络,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不涉政治的信息还是有些真实性的。再有就要翻墙看了,通过自媒体比如微信或者其它国外的聊天软件,也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
电视我看得很少,我认为中国的电视要不是娱乐节目,要不就是洗脑节目。歌颂伟光正的,就是洗脑节目,比如抗日神剧,明明国民党抗日,中共没有抗日,它就说自己抗日,那是假的,你还看?有些事情不符合史实的,很多的洗脑电视剧,把历史真相全给抹杀了,完全是骗人的。
记者:可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是党媒的那种宣传啊?
余文生:是啊,我们从小接受了太多的洗脑教育,被灌输的都是骗人的历史。小时候,我真是决心要把生命献给国家、献给党,要和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要解放台湾、要解放美国,因为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他们太苦了。小时候它们就这样教育我的!
十一二岁之后,我才感觉我受骗了。我生活的家庭比较优越,父亲在旅行社,能看到港台报纸,白天工作忙,晚上就带回家看。他不给我们看,但等他睡觉后,我就起来看,那时我就接触了外国的民主思想。慢慢地我开始怀疑我接受的教育,这使我上初中高中我都不好好学习,我觉得学校讲的都是胡说八道。
从小就让我们戴红领巾,让我们把一切献给党,那时候没有想过:凭什么献给它?为什么要为它牺牲啊,是何道理?你信我,就要我为你去死;你要不信我,我就让你去死,这不就是制造恐怖嘛,这就是极权政权的表现。
当局掌握媒体,不允许别人办报刊、办电台,别人没说话的权利,它想说什么是什么,它说亩产千斤就亩产千斤,假的嘛,骗人的,官方媒体不可信任。而且现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成为当局的政治工具,让你说假的,你也得当真的说,它经常播一些人在电视认罪,搞舆论审判、媒体审判,未审先判本身就违法啊。
自媒体会好一些,畅所欲言,现在也不行了,有很多因为发表言论就被抓了,言论被删除,我发表的言论经常就被删了,只能自己看到。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可现在连自己说话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言论自由。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现状如何改变呢?
余文生:首先民众要觉醒。现在的中国人,思想麻木,明哲保身,不关心别人,只考虑自己,不想想聂树斌、贾敬龙、雷洋都是我们身边的人,有一天我们可能变成聂树斌,也可能变成雷洋,可能变成贾敬龙,到那时候谁能帮助你?如果没有人发声,你一个人如何面对强大的政权?不可能。大家真正觉醒,才能改变这个社会体制。
现在觉醒的人不太多,我应该算一个觉醒的,我并没有冲在前面,竟然都被抓了,是当局把我培养成冲在前面的人权律师,培养成为一个人权捍卫者。
要关心政治。中国人大多数不关心政治,很多人在国外,实际上也处于边缘,华人在美国社会没有什么地位,为什么?他只想自己挣钱,别人什么事也不管。他不参与政治,那政治也不会关心你啊,也不会考虑你,你就没有地位。只有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别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改变社会,改变自己的地位。
还要学会思考,凭什么把生命献给党?凭什么爱党?凭什么爱政府、感谢政府?是政府要感谢人民、党要感谢人民!并不是共产党养了我们,不是它给我们吃给我们穿,是我们给它吃给它穿,没有我们种粮食、生产各种物质产品,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生产十斤粮食,它拿走九斤,只给我们一斤,然后它就说是它养活了我们,这是什么道理?
记者:能谈谈您与709事件的关系吗?
余文生:“709”抓律师,我也被抓了。那是8月6号的夜里,警方撬锁闯进我的家门,把我铐上带走了,我被带走的24小时里,也是遭遇变相虐待,限制我小便,非常不人道,侵犯了一个人基本的生理要求。头10个小时我一直背铐,后14个小时正铐,和酷刑也差不多……
放出来后不久,我知道“709”被抓律师王全璋的两位辩护人在压力下被迫退出,我就主动找了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女士,告诉她我愿意给王全璋做代理,这样我就成了王全璋的辩护律师。
为此我去了天津十几次,在侦查阶段我要求会见王全璋,他们一直以危及国家安全等理由,不让会见,不过那时警方还承认我的法定辩护人身份。
(2016年)8月7号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竟然连我的辩护人身份都不承认了,以王全璋曾有声明不要律师为由强行解聘我。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解聘辩护律师,必须有书面通知,我们没看到解聘我与程海律师的书面通知,所谓的口头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效用。
“709”可以说是中国的“小文革”,小型的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几天内,搞运动一样对律师、人权捍卫者进行打压,这是只有法西斯国家才会有的事情,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发生了。
经过律师及家属的努力,“709”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关注。我非常佩服那些“前仆后继”做这些工作的人,作为王全璋的辩护人,我做了一定努力,我要继续努力,争取让王全璋尽早回家。我是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的委托人,她是非常坚强的女性,也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我对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支持、尊敬,也为王全璋有这么好的妻子骄傲。
记者:前一段时间,您曾经去找过王宇律师?
余文生: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时我被抓,王宇做我的辩护人,包括她的丈夫包红军,都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外面的努力,我可能也像别人一样被起诉了。当时被逮捕的有33个人,就我一个人只关了三个月就放出来了。
据说王宇现在出来了,但谁也没有见到她,我认为她目前仍是失去自由状态,可能是被软禁吧。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商量,我们必须去看看她,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去了她老家内蒙,结果也没找到她,可以证实王宇根本就没有真正恢复自由。
记者:您现在是被监控状态的吗?
余文生:我被放出来之后,当局对我严控,周围都有监视,有时候被跟踪,现在我也习惯了,我也不怕被跟踪监视了。
我在微信发过这东西:七步之内,伏尸二人,还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许有点莽夫之勇、以死相拼的意思吧,起码表达了我的心理状态:我无所畏惧,我不害怕。但确实我要考虑别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我倒无所谓。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一个地方吃饭,警方就给我旁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在哪吃饭,是不是和敏感的人在一起,叫他回去。朋友抬头一看,头顶上有个摄像头,我们在这吃饭被看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才知道,很多摄像头都能调动,当局只要想调,都能调来,防不胜防。在中国没有安全的地方。
记者:您在当前状态下如何保护您的妻儿?
余文生:“709”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让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国,因为确实律师家属往往都被株连。但我的妻子不愿意和我分离,如果我出不去,她不能接受分居两地,她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她一直没出去。
我是不想出去。我留在国内还能做一些事情,为人权事业做些贡献,我自己尽量规避风险吧。我也尽量减少给她带来危险和担忧,我和她有专用电话,让她随时能找到我,而且我会把一些情况及时地通报她。
但是当今的中国,谁也无法保证真正的安全,因为面对强权,以我自身的力量根本保护不了妻子和孩子,谁都保护不了谁。想想60年代的所谓“大饥荒”,几千万人被饿死,谁能保护谁?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家人更保护不了,大家都可能被饿死。
上次是警察撬锁进家把我抓走的,当着我的老婆和孩子的面,没有原因。它觉得你不听我的,就可以把你抓走,它手里有枪,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它可以杀任何人,甚至有一天它可能会剥夺我们的生命。过去几十年里冤杀的太多了,不是用手指数出来的,它是一个数字,几千万,它不在乎再多制造几个数字,在它的眼里,人的生命无所谓,权力才是有所谓。
在中共统治中,很多人要喊民主,就会被剥夺生命,这些人太多了,张志新、林昭等等,都是这样付出生命的。刚建权时,它先杀了几百万的“反革命”,所谓的“大饥荒”又饿死四千多万,文革又整死了几百万,它执政六十多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准确数字无法统计。
现在的社会和过去比起来,因为内外的努力,表面似乎进步了,但“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倒退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现在它们要想抓人,随时可以抓任何人。
可是当局毕竟口头喊民主、自由、法治,毕竟它披着民主的外衣,他们还不敢把这外衣脱掉。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求它实质上的自由民主,用它的法律保护我们,做一些事情去唤起更多的人觉醒。如果大家都觉醒了,民主自然就会实现。当然走在前面的人,可能付出各种代价,可能会付出生命。
据我所知,“709”的律师都受过酷刑及变相酷刑,这是当局对政治犯的常规手段。当局为维护它的统治,一旦被抓就必须让你屈服,不按它的要求做就会野蛮地使用酷刑,如果不屈服,你就会遭遇生不如死的状态。
如果真有一天它再把我抓走,我会坦然面对,哪怕付出生命代价,那时我希望国际社会、公民捍卫者能照顾好我的妻子、孩子。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