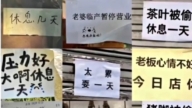中国的改良主义者们历来不乏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故无视对手(他们称为合作者)多年来积久磨练而成的阴毒和老辣,从始至终认为“恶狼可以改良成绵羊”,于是单纯地将自己的理想进行唯我意识设定,用一个虚无的和平理念一成不变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专制“八卦阵”,依靠善意和诚意乞求专制赐于国民一份丰盛的民主大餐,或是自豪地将与暴政的互动关系硬性看成是自己一方的主动引领,有意淡化自己在现实中的“被暴力”现象或干脆视而不见……如此种种不合乎逻辑的一厢情愿之举,多年来早已被证明难撼专制一发一毫,民主大业亦未有尺寸进展之功。
一再批评“和平非暴力”的改良主义,并非骨子里完全拒绝此类行为,而是在亲历了早期对和平梦想的无限推崇,到梦想渐渐被无情现实一次次击碎的严酷过程之后,认为面对暴政的步步紧逼,单凭产生于民主国家的这只“改良杀手_”不一定能够降服中国的专制“恶龙”,这种单极主义的纯种改良,正逐渐失去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已到了不得不对其进行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且必须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中式策略相结合,由守势改进为积极的攻势,或方可为我所鉴。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
民主运动就是要防止暴政进一步“烧人、灭口”。如此浩大的政治工程,必然也是一场牵涉广泛的革命运动,在技术层面总要有超前的思路和备用预案。其发展链条依次略为:
1、 和平非暴力
2、 不合作
3、 维权抗暴
4、 暴力革命
如果以最初级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即可取得民主的成功,当然是上上之选,如若此理念已经对专制暴政无能为力并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则必须要尽快步入民主的第二阶段,跟接第三阶段,即“不合作和维权抗暴” 运动,其后视情况依次类推,力度叠加而求。
“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应验的有国外的路德金、拉甘地与曼德拉诸位,不过其成功是数力并用的综合结果,而非毕一功于一役之现。
若用“爱国主义”的视角搜遍中国,其实也有一位同样让人尊敬的早期“不合作”运动的鼻祖–“五柳先生”,即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傲人风骨,“归去来”的不合作意志,“觉今是而昨非”的大彻大悟眼光,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再后来还有笑傲江湖“不可屈身事权贵” 的诗仙李白,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这类藐视权贵追求个性独立的斩闻逸事屡屡不乏其壮,前后相映生辉,虽不一定是现代民主意识的实践,却是某种人文意识的暗合,亦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之一。
“不合作运动”特别需要参与者具备一种素质,那就是在与权贵决裂后,须经受得起二次富贵的引诱、多次贫穷的折磨和经常性的暴政打压这些考验,这是颇值得国人领会和反思之处。
做为深受源自于欧洲的马列邪教的中国人,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国人必须认清暴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嘴脸,认清其一切改变只为维护暴政而非“恩宠”人民的事实,及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从精神上远离赤祸,从物质上减少关联,使之失去民意和物质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尚不变乎?
二、民主革命的高等手段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手段,以求非常之效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已到了专制与民主二选其一的阵痛期和转折期,死守单一而无效的“和平非暴力”理念,无异于放弃民主,而给民主添加一些新鲜的佐料,对现有思路进行整合,则即刻光明显现。
坊间有多种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见解,想来实在也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其中可取之处在于从根本上动摇暴政的思想基础和民意基础,通过整合“启蒙、和平改良与非暴力、维权抗暴与有限暴力”诸手段,上下互动,内外联动,从软实力上瓦解暴政,从硬实力上压制暴政,多管齐下推进民主启蒙和法制构架建设。
民众之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总是“吃亏”,是因为暴政已毒入本体,根本不认道德公平而只认武力,是因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故欲治之,须下猛药以毒攻毒。做为尚处弱势一方的民主力量,在策略上应当“以民主促进民主,以专制对抗对制,以和谐完善和谐,以危机拯救危机,以宽容理解宽容,以强势压制强势”,保持与暴政对等的自卫权利和能力,必要时做一些实力宣示(如网民的参政议政,现实中的维权抗暴),以彰显气势,压制专制,才可能在漫长的民主进程中争取一席立足之地。
“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陈永苗: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
几百年前的卢梭说过,在暴政面前,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力。中国民间社会至今力度最大和最轰动的一些抗暴维权事件,如瓮安暴动,陇南暴动,不可谓不暴力,不可谓不动乱,可其中利益受损的群众,有几人为自己的种种血泪付出后悔过?在他们的心中如果有所痛心的话,不是太“乱”了,而是太不解恨了。
“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曾节明)。维权抗暴有别于暴力革命,是意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社会变革的最大成功。这种变革当然不是动乱,也不一定必然导至动乱,得过且过保旧守成才是坐等暴力革命来临的主因,因为民主革命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争取民主和公平,决不是为了“杀人”。
从悲天怜人的人文情怀上说,老天不会特别钟情于一个暴虐的恶魔永久为害人间;从正反互制,阴阳平衡的角度看,只要世上还有不公和暴政存在,受压迫者总会寻找到一种与暴政对等的反抗手段和方式(如网络科技对诸多现实行为的替代作用)与之相抗衡,在旧的反抗手段(如冷兵器的淘汰,战争空间的缩小)失效之后,又会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到另一种可行的新途径,手段的多样性并不会随着科技的发达而呈反向的递减。
不过,任何希望在人类短暂的生命过程中总是显得很遥远,但这个“遥远的希望”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也许正是新兴革命手段进行酝酿和成熟的必须过程。
2009-06-17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