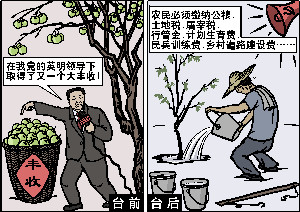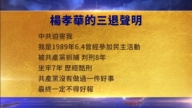父親如果在世,今年100歲了。他的前半生,在民國時期;後半生,在中共時期。他多舛的命運是從1949年中共篡政開始的。他經歷了不少事,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踹寡婦門,掘絕戶墳,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政權!」「共產黨反對的,十有八九都是好事。」
中共篡政後,灑向人間都是怨。然而,對那些罪惡歷史,很多經歷過的人,在有意無意的淡忘;孩子們,或許連知道都不知道了,因為教科書在刻意粉飾歪曲篡改。
但願年輕一代永遠不知道什麼叫恐懼和歧視,但願父輩們所遭受過的苦難一去不返。但是,產生苦難的根源不剷除,噩夢還會再現。還原歷史,了解真相,認清中共,走出迷途,是中國人走向未來的希望。
儘管歲月不堪回首,但歷史真相不容掩蓋。借父親「百年祭」,我試著把一些記憶的碎片撿拾起來,拼兌還原,寫成了下面幾篇短文。雖然點點滴滴,但它是真實的歷史。
我的「反革命父親」
家譜上有記載,父輩管家世代為官,家道興旺。可惜一尺厚的家譜在文革中漚成紙漿埋了。聽二叔說,忘了是哪一代上,有個叫管幹珍的說過:「考取功名不做官,我就愛當教書匠。」那前輩管幹珍不但思路格色,脾氣還挺牛!但是,父親既不格色,也不牛氣,聰明過人,博學多才,倒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大半輩子教書匠。
爺爺管毓定,祖籍江蘇常州人。晚清末年廢除科舉制度後,考入北京外語學院前身——「同文館」學俄語。學成後朝廷派他出使俄羅斯任一等書記官,在外駐了5年。史書有記載,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員。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把一隻墨水鋼筆丟了。父親說:「得,你爺爺從俄羅斯帶回來的幾打帕克鋼筆,就剩最後這一隻了,讓你給丟了,絕筆!」以前還見過爺爺帶回來的四套銀餐具。多年後,我在法國朋友家的玻璃櫃里見到了,拿在手裡同樣沉甸甸的。
爺爺28年在北京病逝時,父親12歲。父親幼年接受家塾的傳統教育。後來進洋學堂,中外文都學了。他能教大學中文,能用日文書信來往,用英文讀小說。
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期,父親在「國民黨政府剿共委員會」謀得文書一職。為此,他被定為歷史反革命。49年初中共一進城,大批象他這樣的國民黨政府留用人員,被轟出北京就業。6月父親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9月被通知離開北京,去石家莊教書,直到92年在石家莊病逝。
到我這一輩,我和我哥都是「狗崽子」。文革68年,我14歲因為出身不好在學校挨批鬥。16歲我進工廠學徒,哥哥去了水泥廠。父親說我是童工,瘦小的哥哥是壯工。即便如此,他說也知足了,如果趕上我們那一屆都上山下鄉,「那你們就是第一撥走的,最後一撥回來的」。
我和我哥都沒有什麼學歷文憑。文革時,我高小四年級,哥哥上初一。上學、參軍沒我們的份。父親手不釋卷,通達古今,拜讀他的博士生排不上隊。但他不催我們去學校進修奔文憑,這似乎有違管家書香門第的遺風。他對我們的低學歷,始終泰然處之。
後來我體察到父親的苦心,他是不想讓我們被洗腦。他自信,我們在他身邊,耳聞目染,得益於他的傳統教育,學到了很多教科書上沒有的好文化。他說過我們的學識、能力一點不差。他甚至指著我對他的學生說,「我幫她備點兒課,她能給你講課」。最重要的是,我們懂得恪守道德,本分做人。對此,我很感激父親。
和尚發展我媽入地下黨我爸不知道
49年我爸還沒離開北京時,見家裡不斷有警察來,就問我媽:來人找誰啊?我媽說:找我啊。我爸納悶:找你幹嘛?我媽說:我是中共地下黨員。我爸急了,問怎麼回事?我媽說有個和尚發展她的。我爸說他怎麼一點兒不知道?我媽說和尚叮囑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我爸問和尚呢?我媽說:好長時間看不見他,最近才露面,他說被國民黨政府抓捕判刑蹲了監獄。他還學舌國民黨法官當庭訓斥他:「你一個宗教人士,參加什麼共匪?滿處串通,禍亂社會!」法官很生氣,重判了他。
那和尚說,要不是國民黨撤離大陸,他還在監獄裡呢。放他出來的人問他,都發展誰了?他說有我北京宣武區的俞淑珍,結果就有警察上門來找我媽。
我媽成了中共地下黨員,這對危難中的父親來說,象有了一把紅保護傘。但是,我爸沒沾光。這邊,政府讓我媽在49年的「十一」,開國大典時上天安門觀禮台當貴賓;那邊,組織上轟我爸出北京,「十一」前必須離京。
後來我爸跟我們說起這段歷史,說他在國民黨剿共委員會幹事,但是不知道自己老婆是中共地下黨員,這真是個不小的諷刺!
我爸對和尚秘密發展我媽入地下黨很反感。他說中共能在我們家搞,也能在別家搞。讓夫妻、父子反目,很卑鄙無恥。國民黨也有特務系統,他們專門有一幫人干,不象共產黨這樣無孔不入,不擇手段,波及到全社會。
大哥12歲當了北京「小英雄」
49年,中共以血腥暴力奪權篡政,毫無合法性可言。在建政之初,民心不服,立足不穩,城市鄉村,各地爆發的反抗相當激烈。
我姥姥家住的北京宣武區大雜院里有戶人家,他家大兒子在國民黨的一個「剿匪團」里當小頭目。「剿匪團」經常在北京一帶和中共發生武裝衝突。那家大兒子被中共通緝捉拿。
姥姥家的窗戶正對著大門外當街。那家人住在里院。一天,瘸表哥(17~18歲,患小兒麻痹症)看見一個大漢從外面進來,大步流星去了里院,進了那家屋裡。大漢的特徵正是通緝的那個國民黨「匪徒」,大高個、左臂帶傷、鑲有金牙。當時身邊還有兩個隨從。
瘸表哥想去派出所彙報,腿腳不利落,又怕驚動了那仨人。他在屋裡正著急,看見我大哥(12歲)晃晃悠悠放學回來了。瘸表哥隔著玻璃,指手畫腳、擠眉弄眼示意他別回家,出去報警。大哥沒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一抬眼,看見了里院的大漢,正舉著有傷的胳膊。瘸表哥見大哥還不明白,接著比劃個頭多高,又指自己嘴裡的牙。這時,大哥突然明白了,撒腿就往外跑。一口氣跑到派出所舉報。
開始警察聽了不相信,還拿他打哈哈。以為就是毛孩子想入非非,想當見義勇為的英雄。大哥急哭了,警察開始認真盤問,發現這孩子說的靠譜,感到事態嚴重。於是緊急行動,組織警力,直撲姥姥家的大雜院。
警察持槍破門而入,屋裡的那仨人沒來得及掏出槍,都被活捉了。
第二天,《北京晚報》頭版報出,說我大哥是「小英雄」。
被擒的大漢,正是那家人的大兒子。那天,他是鋌而走險來探望母親的。槍林彈雨中他沒死,卻死在無冤無仇的鄰居孩子手裡。大漢很快被政府槍決了。從此,那家人成了「匪屬」,誰都不敢沾邊。
轉年是1950年,因我媽當了宣武區婦聯主任,忙得整天見不著人影兒,大哥沒人管,就把他送去了石家莊父親身邊。3月,石家莊鬧腦膜炎,大哥染上了,送去醫院搶救。抽出的骨髓是渾濁的,醫生說,沒救了,我大哥就死了,死時剛過12周歲生日。
幾個月後,大哥的死訊才敢告訴我媽。她前一天晚上知道的,第二天就得了白喉,差點病死。
大哥死得蹊蹺,父親說是「要賬鬼」。我不這樣看。其實,大哥是遭了惡報。中共是邪惡的,剿滅共匪的大漢,替天行道,自然就是好人。大哥和瘸表哥聽信了學校、政府和不明相的大人們的煽動,堅決打擊國民黨反動分子等等。中共灌輸這種「愚忠」,以為舉報大漢是正義之舉,英雄行為。熟不知,這是做了件反天理,逆天意的惡事,害人害己。
我大哥是管家、俞家都喜歡的孩子。他死了多年,奶奶還時常把這個長孫掛在嘴邊:你們誰也沒他懂事!才幾歲啊,就知道我不愛見家裡丫頭們哭哭咧咧,只要兩個妹妹哭了,他馬上過去哄,還安慰我:『奶奶,我推推他們就不哭了。』從小就仁義、孝順,老天爺怎麼把他收走了呢?
好人應該有好報,但是得順天意,才能躲劫難。
在中南海看門的瘸表哥出事了
隔著玻璃窗攛掇我大哥去派出所報案的瘸表哥,是我舅的兒子。聽我爸說,我媽家原來不窮,家裡有人抽大煙給抽窮了,把老俞家抽成了「城市貧民」的成分。
瘸表哥的爹是大煙鬼,他見老婆跟別人跑了,自己也扔下殘疾兒子跑了。多年沒他的音訊,都以為他死了。沒想到他參加了「八路」,和國民黨軍交戰時被打死了。咽氣前,他託付跟前的人,說他北京還有一個兒子,叫俞念祖,在哪哪住。後來受託人把信兒送到了。於是,瘸表哥就成「烈士遺孤」了。
瘸表哥從小就患有小兒麻痹症,加上文化程度不高,不好找工作。他成了烈士遺孤,又有舉報國民黨匪徒的榮譽,再加上我媽正大紅大紫,上邊給瘸表哥安排了正式工作——去中南海看大門,就是現在的那個新華門。瘸表哥覺得自己一步登天了。
不呈想,沒幹多長時間,他不但被停職了,還連人帶戶口被轟出了北京。聽我媽說,中南海里的人反映,瘸表哥有作風問題,看大門不規矩,老是盯著出入的年輕女同志。
家裡人都數落瘸表哥沒出息,把好差事給混丟了,沒造化!我媽說也就是多看了幾眼長相漂亮的,能怎麼樣?那裡邊的女人,不是領導的千金,就是領導的新老婆,漂亮的是來陪首長跳舞的文工團演員。我媽直後悔,說當初要是不巴結這份中南海的「闊差事」,換個別的什麼工作,可能就出不了事了。
67年,全國各地停產鬧革命,瘸表哥自稱是「逍遙派」,從下放地陝西跑回北京幾趟。他說自己改名了,不叫「俞念祖」,改叫「俞念東」了,意思是,拜祖宗沒用,改拜毛澤東啦。
瘸表哥在陝西一個小縣城的機械廠當工人。後來他娶了個農村媳婦。我記得,她有隻眼睛失明,安的假眼球。他們的孩子傻乎乎的。看得出來,一家人日子窮困潦倒。在那個講究家庭出身的紅色年代裡,「烈士遺孤」、「俞念東」都沒能給他帶來好運。
父親說瘸表哥的變故,最能說明中共推崇的「出身論」、「成分論」很荒謬。「烈士遺孤」的紅帽子戴在他頭上了,又怎麼樣?他從小缺爹少媽,沒家庭教育,沒德性,品行差,幹什麼也不幹好,看個大門還無事生非呢。「子不教,父之過」。
瘸表哥一輩子不得志,依我看,根本原因是遭了惡報。他害了大漢一條命,攛掇我哥一個未成年的孩子舉報,也坑害了我哥。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老倒霉,愚蠢到數典忘祖,更名改姓,把毛澤東當救星,結果是更倒霉。
四舅「不愛江山愛美人」
俗話說,一人得勢,雞犬升天。我媽當了宣武區婦聯主任,我姥姥家好幾個人都沾光,入黨、提干、就業。瘸表哥被安排去中南海看大門,四舅升任宣武區下面一個派出所所長。四舅是我幾個舅舅里話題最多的一個,他「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段子,在家族裡是一大美談。
我印象中的四舅母很漂亮,高挑個兒,白凈臉兒,明眸潔齒。聽家裡人說,做姑娘時更可人兒。她就是那大漢的妹妹。她家出事後,如花似玉的姑娘沒人敢娶。
四舅找對象眼高,挑剔的厲害,所以一直沒成家。不知道什麼時候,四舅相中了大漢的妹妹。家裡人都反對。
四舅偏要娶,組織表態也堅決不準。上級派人來勸導,見勸不動,最後攤牌:「你是要這身『老虎皮(指警服)』,還是要『匪屬』(被鎮壓的反革命家屬)?」四舅沒猶豫,當即脫下了警服,當著領導的面,把「老虎皮」扔在椅子上走了。
四舅到底還是娶了「匪屬」做老婆。付出的代價是離開北京去外地工作。他帶著老婆和「永遠不得回北京居住」的驅逐令一道去了長沙。
婚後,四舅和四舅母十分恩愛,先後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都長到一米八以上的個頭,魁梧英俊。多年來一家人過得其樂融融。他們回北京途徑石家莊,來看望過我們。
多年後回頭看,倆人是美滿姻緣。想當初,結婚非要「黨組織」批准不可。組織認為,四舅和四舅母屬於不同「階級」地位,所以不同意他們結婚。四舅認為,他不能昧良心,他們同住在一個大院,知根知底,四舅母和大漢一家人不是壞人。在黨性與人性衝突時,四舅選擇了人性,沒聽黨的話,沒跟黨走。正是因為四舅善待了「匪屬」,選擇了良知善念,他有了福報,夫妻恩愛,兒女雙安全,一生順風順水。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