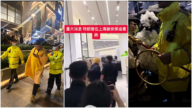她的兒子沒了
大陸媒體人 周折 採訪手記
11月25日,我在慧忠裡407號樓的大門內見到王靜梅。
盡管見過她的照片,還是沒能一眼認出她。她一米五左右的個子,一身暗色調,捆著直發。臉盤很圓,體形偏胖,但顴骨高高地凸著,臉頰有點凹陷。紋過眼線和眉毛,有些年頭了,略略地褪色。她看到我,目光很柔和。
這個剛接到兒子死刑判決書的母親是平靜而無助的,沒有想象中的凌厲和銳氣。
“是王阿姨麼?”我有些怔。她輕輕點頭,示意我和身後的大批人馬上樓。樓外面不遠的長石凳上坐著幾個年輕人,24小時不間斷地警覺著樓下的過往行人。有時裝作不經意地站起身跺腳,“好冷啊好冷啊”。
她的背微駝,上樓梯的時候身子往前傾,似乎背負著無形的擔子。
跋。一樓,二樓,三樓……一群人的腳步聲在五樓停住,擠到501室裡。
她的家是亞運時代的回遷樓,六十來平米的二居室。家具大都是黃色,被各種日常用品塞得滿滿當當,隨著年月班駁。
將近十二月的天,床上還舖著涼席。7月1號,她被帶走,在公安局密不透風的精神病醫院呆了四個半月,直到11月24號才回家。
而她回家最叨掛的,不是上海監獄裡已經被判處死刑、只待一聲問斬的兒子,卻是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家,滿冰箱壞掉發臭的菜,還有消失的耗去她八年心血的上訪資料。
四個半月,她在醫院十平米左右、裝著兩台監視器的小屋子裡,不能讀報,不能看電視,不能和生人說話。可以出門去小花園逛逛,但有護士的“庇護”。
為了更好地掩護她,她一度掛上老實巴交的化名,“劉亞玲”。醫院是在北京郊區,旁邊是潮白陵園。起初的128天裡,沒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哪裡,火急火燎的家屬滿世界找她。
一個被與世隔絕的人,哪裡知道外面的天翻地覆。
11月23日,她重見天日。有關方面終於人性化了一把,把她送往上海提籃橋監獄見兒子,談話不得超過20分鐘,不得談案情相關。
母子倆久別重逢,兩個人都很平靜。她對兒子說,在裡面要注意鍛煉身體。兒子點頭。末了,她給兒子留了1000元錢,獄警代收下了。
她問上海的法官,兒子有救嗎?徐法官很認真負責地說,回去寫申訴材料吧。
於是,尚未在精神病醫院辦理出院手續的她被送回北京家裡。順利得不可思議。
見到兒子的那個晚上,她約了前夫。前夫帶上了北京律師,她卻不留情面地把手一揮,律師根本沒用!她也抗拒媒體,媒體和律師一樣,一無是處。
她對他們不緊不慢的說,兒子一定是死緩。言之鑿鑿的理由,僅僅是法官讓她寫申訴材料了,還有,兒子的二審判決書上並沒有說,死刑立即執行。
誰也沒有再多說什麼。他們不忍心用一種殘忍的可能性,去擊碎母親的臆想;他們心底也存著一線生機。
現實的車輪卻沿著既定的軌道,不可阻擋地向前碾,猝不及防。
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她收到了兒子的死刑復核意見書,死刑,立即執行。突然間六神無主,渾身酸軟,像抽去了筋骨,一灘泥似的往下墜。
她打電話給姐姐,給前夫。而他們打電話給我們。很快,十幾個人擠到了家裡。
她感覺被愚弄被欺騙。她追問著每一個人,社會怎麼會是這樣?大家無言以對,即便有,也只是一聲嘆息。
她的聲音終於哽嚥下來,坐在床邊,對著牆壁,無聲地顫抖。很久沒有這樣哭過。上訪多年,她習慣用強硬的姿態回應冷漠。
人越來越多,親戚,街坊,律師,記者……有人掏出照相機和攝影機,在屋裡地閃著燈,有人不停地追問,你跟兒子的見面情形怎麼樣,有人跑進兒子的房間,看到兒子床頭《魔鬼司令》的海報,施瓦辛格的肌肉閃閃發亮。
她越來越無法忍受,那些陌生的臉孔沖進屋裡,要見証並且記錄她的悲哀。
而她的兒子就要死了。
她提高分貝,你們走吧,你們走吧!
準備出謀劃策的人們愣住了。但又都理解了母親,一個個起身告辭。也許這件事情真的無力回天。
臨走前我送給她一本雜志,裡邊是她兒子的庭審記錄和辯護律師們的羅生門。功利地說,我想贏得她的好感,為自己再一次見証歷史打基礎。
她翻開花花綠綠的雜志,看到“襲警”的黑體大字,突然間炸了:“憑什麼說我兒子襲警?你們媒體都在亂七八糟報道些什麼呀!”
她倉促地掠過那些案情疑點和事件追蹤,把手指停在兒子的二審照片上:“我只要這張照片,你把它給我就行了。”
找不到剪刀,她就把兒子的照片從嶄新的雜志上撕下來。
硬生生撕了下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所有的新聞媒體都頭條報道,她的兒子已注射死刑。沒有人回帖,因為所有評論功能被關閉。
兒子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靜,在九點左右的時候,注射死亡。他死的時候,她還在屋裡寫她的申訴狀,她要緊急吁請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她要兒子。
人們遲疑著,要不要驚擾這位奮筆疾書的母親,她兒子已經死了。
不想告訴她,就連她的兒子。
11月23日上午,提籃橋監獄的會見室裡。兒子隔著玻璃,對母親微笑。他說,不要擔心,他一切都好。
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他就要死了。
*****************************
http://www.youtaker.com/悼念中國抗暴英雄楊佳 最新版 怒放的生命
轉自《阿波羅》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