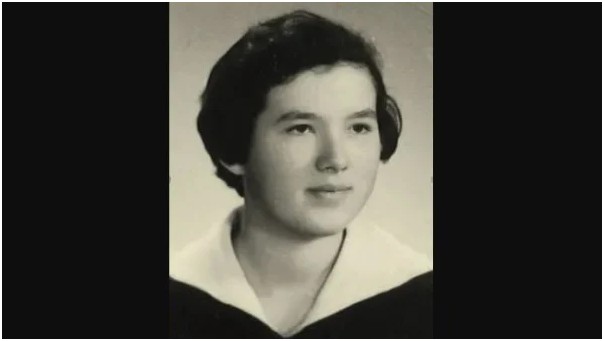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5月09日讯】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时,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当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01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纽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因为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而父亲不但是军人,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权眼睛里,他无疑是“敌人”。于是自从抗战胜利离开中国,父亲再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每当我读到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
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书将我引进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门。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远,只知道,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与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现在两位老人家都到了一个可以尽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因为我曾经成功地为他们传递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舒先生好讲故事,但他需要一个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02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卡玛・韩丁的父亲那样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
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学校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那里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打倒美帝”喊声震天。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烤得我心里发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还站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倒是常常想到那个温和友善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练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练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练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会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雷打不动。
03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限,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
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时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后来,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们一行出发之前,副市长崔月犁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说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未完待续)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