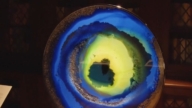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记录她从1993年开始追随自己的师父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去听讲法的过程。她平实细致的讲述中,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江泽民这么狠地整法轮功,为什么在严重迫害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坚持学法轮功。现在有很多人在追问:江泽民为什么这么妒恨李洪志先生,为什么要用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把李先生引渡回国,为什么这么害怕法轮功学员,总得有什么原因吧?我想,这篇有着特殊的历史跨度、详细记载着法轮功创始人在大陆传法时许多具体事例的文章,会帮助很多人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具体答案。
文章虽长,可读下来真的感触良多,特此推荐给尊敬的读者朋友们分享。
* * * *
法轮大法九年洪传纪实图片展──《正法之路》即将展出,看到这栩栩如生的昔日的照片,不禁想起了这多年自己伴随着大法在世间的洪传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想尽力写一点出来能够作为证实,献给这个在师父的亲自指导下,历经八个月的挑选制作终于完成的伟大作品。
我从年轻时就有病,总在看病吃药,多年下来对医生、药物已没信心。92年底,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由家人搀扶着上飞机来到北京找气功师。找到的气功师给排呀补的治了许久也没解决根本问题。93年7月在一个朋友家里闲坐,看到书架上有一本《法轮功》,随手拿下来一翻,上面说,给修炼者的小腹部位下一个法轮。我当时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能知道生命的奥秘,气功师能造出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体来,真不可想像,这件事太大了。又一想,有一个法轮在小腹部位,那一定能治我的病,就急切地请这位朋友帮我去找到法轮功。
7月25日我参加了李老师在北京举办的第11期法轮功传授班,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
我是48年出生的,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气功、修炼一切都没有概念。虽然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学生是为考分,也谈不上信仰,所以脑子里是空的。
11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我坐在二十几排。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聚精会神地听,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这些事这几年自己也想过?
我们这一代人在豆蔻年华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但面对这茫茫的世界,心里很苦,不知用什么基准来衡量它,用什么标准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工作单位,整日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包围着,心里十分厌恶。闲下来时总喜欢看《奥秘》这类杂志,思索人生以外的问题,这时的心在人世外飘荡,感到轻松自由。
今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每堂课我都津津有味地听,每天从课堂上下来,身体的难受程度都缓解许多,每天下午都早早准备着上路。一期学习班结束了,我想再能参加一期就好了。听说十二期在五棵松的某单位礼堂,我赶紧找着买票。五棵松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几堂课后我开始发烧,咳一声嗓子连着心疼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老学员跟我说,再难受你也要坚持来。三、四天后烧突然退了,感到难受的地方好大一块东西没了。之后我又参加了第十三期,在“二七车辆厂”,更远,先坐车到西便门,然后乘309路郊区车到终点。每天下午4点多就上路,7点半开课,回到家12点多了。三期班下来,我辞退了保姆,自己可以料理日常生活了。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
我小时候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住过几年,关于佛、道、神及鬼的概念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太太们讲故事得来的。那时农村没有电,晚上小孩子们常看星星,那满天的星星就是满天的故事,每颗星星上都载着一段离奇的传说,一切美好的憧憬,一切不可知的秘密,都在那遥不可及的天上。小孩要做坏事了,老太太们就用鬼来吓唬他,还告诉他有因果报应。童年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长大了上学了,学校老师说:这些都是没有的。进城了,城里人都很现实,不讲那些看不到的东西。自己也从未仔细想过。今天这个题目一下子摆在面前,真有点头晕目眩。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功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堕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

北京十三期结束后,再下一期是武汉,我还想听下去,但独自上路对我来说很困难,虽然身体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原来底子太差,所以那时还是连暖壶也拿不起来。想来想去别无选择,我还是壮着胆子上路了。我的票是中铺,其实爬上去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上车后坐在下铺,下铺的主人也不赶我,想喝水刚一弯腰,边上的人马上帮我倒。到了晚上,下铺的小伙子突然说:“你睡中铺行吗?不行我和你换。”我很不好意思,就说先试试吧。好不容易爬上去躺下,一会儿就觉得晃得像在大海上一样,难受得不行了,又爬下来说,我还是和你换吧。他二话没说就上去了。在汉口下车时,同车的人还帮我把行李拿到站台上。当时只觉得很幸运,多少年后才明白,是师父在管我。那次武汉连办了三期,即武汉的三、四、五期,第三期在武昌的财经学院,第四期在汉口的市委礼堂,第五期在武钢。武汉三期后已是10月中旬,下期办班是广州。我又跟到广州,参加广州第二期传授班。
老师每一期讲的都大致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讲同样的问题时,许多话都是一样的,有时就会换一个角度讲,只几句我一下就茅塞顿开。就这样越听越明白,越听越觉得事情大得了不得。其实老百姓对佛的理解就是帮人消灾解难的菩萨,对于道的理解就是惩恶扬善的义士。渐渐地我心中清晰地感到老师讲的理高出了佛和道,那就是普天的理。老师能造出法轮来,老师能这么清楚地了解生命,能给你消业,这可不是一般的顺顺气。那么老师是谁呢?我紧张地不敢想下去了。这件事可大得了不得。我让我先生来学功,又给国外的孩子打电话,让她尽快回来听课。
那时只要能打听到消息,老师在哪讲课,我就尽最大可能去。要想一期期跟得上,就得在这期班的最后一天晚上上完课就奔火车站,那就要在这之前买到火车票,可在当时大陆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到一个地方还要尽可能找到便宜的地方吃住,以便维持较低的费用。有时也想停下来缓一缓,可每期班结束时老师的话都使我激动不已,下决心再跟下去。记得天津第二期结束时,老师第一次提到要把这个法给大家留下来。这个“留”字在我头上炸了一下,那就是说这件事不会永远做下去。那次我下定决心,只要是老师在这个地球上讲课,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能够得着,我一定要去。那时我有一只拉竿的旅行箱,在当时国内算是高级的,里面有电锅、米、调料、录音机、磁带、电筒、衣服、雨伞等等。当时油盐都吃不下,最容易吃的是牛奶和稀饭,所以到一个地方要自己煮点。拖着这个身体,跟上老师的行程,确实困难。再难只要一开班,坐在课堂里,看到老师走上讲台,什么都烟消云散。那种喜悦从心中生出,那种亲切无法形容,只感到无比的伟大、无限的光辉,人间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想追随着老师那神圣和壮丽而去。每期班最后老师都希望大家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我总是很抱歉,一篇也写不出,祛病健身,感恩戴德,心里都没有,心中时常涌动着一句话,就是:愿老师永远与我们同在,愿老师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生命的道路。
记得94年4月,我从合肥第二期学习班回到北京,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累得不得了。下期是长春,长春是老师的家乡。俗话说,人杰地灵,去老师的家乡看看,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又上了火车。车到了长春站,长春的学员举着牌子轮流值班接外地来的学员,我们被安排到离城中心较远的一个旅馆,因为那里很便宜。一路上带队的长春学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着情况,大家初来乍到都很新鲜,早忘了疲劳,都高兴地从公共汽车的车窗向外望着。忽然,这位长春学员手指着远处说:“快看,那是老师的家!”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极普通的没贴面的砖楼,顶多四、五层高,老师这么大本事却住在这样的地方,太不容易了。大家心中默默地升起敬意,半天望着不说话。

那次开班在吉林大学的鸣放宫。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很多,老师办了两个班,早班上午9点~11点,晚班下午7点~9点。早班的票我早就买了,可晚班的票买不上。第一天上午下课后,回到宿舍总不定神儿,我们是来听课的,明知道老师晚上还在上课,可我们在宿舍里呆着,不是味儿。第二天上完课,我们没回旅馆,在礼堂外的草地上呆着,一直等到晚班开课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希望能买到退票进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一群人眼巴巴地望着。突然一个学员在我边上说:“谁要票?”我很高兴,一把拿过来,把钱塞给他。我高高兴兴地走进礼堂,准备落位,只见一个熟悉的老学员远远地奔过来喊:“我正到处找你。”我想:“完了,这张票是保不住了。”果不其然,她说青海来了一个学员,第一次来听课,普通话听不太懂,想再听一遍,你是老学员,把票让给新学员吧,她是第一个从青海来学的。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票交出去,就又站到了大门口。人都进去了,早就上课了,我们这些没票的仍在门口站着。这时礼堂的管理人员把正门关了,零星出入在侧面的一个小门,我们就向那小门走去。在离小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青人,刚才我就看他站在那里,也不吭声。当我走过他时,他忽然问我:你要票吗?我一愣,马上脱口:要!他把票给了我,我赶紧把手里攥着的那位青海人给我的票钱塞给他。我又有票了!看着周围羡慕的目光,我很不好意思,就对边上一个也是老跟班的郑州的小伙子说,你进去吧。他说:这是该你去的,你就去吧。当时鸣放宫的地下室在办舞会,买张舞票从小门进去就可以到听课的大厅,可大家都没这么做。天津的一个小伙子说,如果我们做了这样骗人的事,即便能进去听课,也什么得不到。后来听说,我进去后又过了很长时间,礼堂的看门人看到学员这样的锲而不舍很感动,就把守在门口的学员都放进去了。
那期班,我们分小组和老师合影,大家自动组合,老师挨个和大家一起照。老师每天从家中走去上课,有的学员有开车的方便,想请老师坐车,老师都婉言谢绝了。
我们住的旅馆离吉林大学很远,那时公共车票还很便宜,只要几毛钱,有的学员每天很早就上路。有一次我问一个学员,这么远你怎么不坐车?他说:爱人不支持,所以他一分钱一分钱地省,能攒出点钱,就又可以参加一个班。我听了很感动。这是老师在家乡办的最后一期班,最后一堂课结束时,老师给家乡的人说了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我和几个学员的车票,开车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了,可大家还在听老师讲话,不愿走。离开鸣放宫冲到马路上,只剩十几分钟了。我想赶不上火车可麻烦了,票是很不容易才托人买上的,是硬座而且要到天津再转北京。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帮帮忙开快点,十分钟赶到。出租车在车站广场的外边停住了,离站台还远的很呢,只有几分钟了,也不知哪个站台。天津的小伙子提着我的沉重的箱子飞也似地跑,几个人扛着行李飞跑,什么都来不及想,进了车站径直上了站台,也没走错,只见天津的小伙子一脚踏上火车扑通就跪倒了,火车瞬间就开了。那天真是奇迹。
听说5月29日在成都办班。前面的一期是重庆。我想成都以前没办过班就没有法轮功辅导站。一路上见到老师这么辛苦,在天津办班时,住的是二十几元人民币的旅馆,不能洗澡。我们听完课回去睡觉,可老师24小时都在给我们调整,就这样还有人硬是找到老师的住所,进去磕头不起来,让老师给他家里人治病,老师怎么讲也不听。面对这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心都有,老学员心里都很难过,从来不到老师跟前凑,希望老师能多休息一会儿。当时我先生在成都工作,我想利用这便利条件,看看能帮点什么忙,于是就先去了成都。到成都找到气功协会,说我可以出车,有什么要做的,我一定尽力帮忙。气功协会是自负盈亏的,办气功班是为了挣钱,所以很抠门。
那天老师从火车上下来,同车还有很多从重庆跟过来的学员,已是5月下旬,南方已很热了,车里没有空调,个个风尘仆仆,随行的工作人员背着大捆大捆的书──《法轮功》(修订本),汗流浃背。气功协会来了一辆夏利出租,老师让同行的人拿着东西先走了。我先生去停车场想把车开到出站口,让老师少走几步。车刚出停车场,顿时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水泄不通,也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车,幸好我先生的车是进口的,自动变速,所以启动快点,使出浑身解数才冲出包围,急得嘴里起了一串火泡,结果让老师足足站在车站前等了四十几分钟,我心里这份抱歉好几天都平静不下来。后来听老师说这是干扰,一路上碰到的这些麻烦太多了。
成都的班在一个招待所的礼堂。老师办班从来不做广告,那时各种气功班多了,人们也不在乎,所以第一天开课人没坐满,可一听老师的课就大不一样,于是消息急速地传开,到结束时已有800多人。每天上完课,我先生开车送老师回旅馆,大家都磨磨蹭蹭的看到老师上车了才回家。能为老师减轻点疲劳,心里非常高兴和安慰。
我们的班是独立的,既不和社会上有什么交道,气功协会也只收钱。老师出来传功,行程、食宿都要自己安排,实在是太辛苦了。
在成都的那段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我跟随老师去了许多地方。头一天是去文殊院。我们的车在前面,同车的还有一位香港的商人,他听说成都要办班就一直在成都等着,他的国语说不好,所以听课有些困难,老师一路上在给他讲解。下车了,后面的车还没上来,我们就先进大门,老师走在前面,一进门两旁站着四大金刚,老师回过头来跟我说:我讲课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我说,他们怎么这么难看呀。老师说:他们威力很大的。那时庙里很乱,狐黄白柳什么都有,老师所到之处都在清理,只一挥手就行。

(明慧网)
几天后,老师去青城山,同行的有大连站长、贵州站长、武汉站长和其他几位学员。那次我突然明白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思。我这样的身体居然爬上山顶又走下来。回来后,我先生的同事大吃一惊。成都班结束后,我们和老师去了乐山和峨眉山。在乐山的罗汉堂里,同行的一位功友跑过来跟老师说,××菩萨(我现在记不清名儿了)说,见到老师很不好意思,向老师行礼。老师说,我们走时他们会送出去很远。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我只能看到一个个泥巴塑的像。出罗汉堂时,后面的和尚在说,这群人了不得。显然他看到了什么。峨眉山确实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在金顶我对天目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感觉。跟着老师走了一圈,神的事情太多,我的大脑有点承受不住,我想起了《西游记》,还有一系列的传说,我问老师:怎么神话故事都成了真的?老师说:神话故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下一期是郑州,好不容易买到了卧铺票,我和老师同乘一次车去郑州。上车那天,天很热,进站时,挤得不得了,老师和我们一样拿着东西,汗流浃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车才知道是加挂的最后一节车厢,和前面不是一个局的,列车是成都局的,这一节是郑州局的,前面的列车不管这节车厢的一切供应,连水也不给,通向前面车厢的门也给锁了。这节车厢上还有其他一些学员。我心里很着急,路上只有方便面,可没热水怎么办?我和同行的武汉学员找了一只水壶,停车的时候跑下去,从前面车厢上去,灌满开水,可跑回这节车厢的时间就没有了,只好在前面的车厢站到下一站再下车,从站台上跑回这节车厢来。这点水也仅够喝水,每顿饭给老师泡一碗方便面。我们和老师一起买的票共6张,是这节车厢旅客的最后一个格子,也就是最后面的车尾了。车过华山时,老师站在车尾,那节车厢后连接处的门上没玻璃,老师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远山。我当时很纳闷,想老师在看什么呢?也好奇地走过去望望。老师告诉我,华山上很多修道的人都下来了,来看望老师,跟着火车走。老师问他们:你看我的弟子如何?他们有的都修了很久,说没有几个能比上的。这些人一直跟到郑州听法。后来老师在讲课时讲到了那天的事。
郑州班几乎是条件最差的,气功协会找了一个废弃的体育馆,中间是一块破旧的地板,四周的看台是砖头砌的台阶,残缺不全,古老的窗户有的连玻璃也没有,让我们的老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讲课,真是没法说,老学员都叹口气。6月11日开班,几天后的周末,那天是下午4点上课,课上到中间,突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大雨加着冰雹,铺天盖地下来,雨从窗户“潲”进来,看台上的人动起来向里边拥,一会儿核桃大的冰雹砸下来,体育馆的铁皮顶震得巨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狂风暴雨、冰雹,还有雷电,响作一团。我当时坐在面对讲台左边的地板上,只想自己是老学员,要守住心性,不能添乱,就静静地坐着,尽量挤着点给从看台上下来的人留点地方。冰雹砸得更厉害了,似乎想把这个屋顶砸通,老师的讲台上方屋顶漏了,雨水哗哗流下来,紧接着跳闸了,灯灭了,一片漆黑。这一切发生只有几分钟。大家望着老师,有的静静地打坐,我心里在着急,怎么办呢?只听老师说,谁在上面?再看老师微闭双目,双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胸前。跟前的学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有学员在讲,快看老师的手上。一会儿老师用手一攥,好像把什么东西抓在手里,随即把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把水喝了,然后把手里的东西装在了瓶子里。这时雨停了,太阳露了出来,阳光照进了屋子,大家鼓掌欢呼。之后老师坐在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老师说,我给你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把很多东西摘掉了。这时灯一个个亮了,继续上课。事后,经常跟班的一个郑州小伙子说,当时他在控制室,跳闸后线路上一直没有电,可灯却一个接一个亮了。那天下课后,出来看到街上的树劈了不少,卖冰棍的老太太拉住我们问:刚才的事是你们招来的吧?我吃了一惊,老百姓居然也懂这些。第二天郑州的报纸报导许多地方屋顶都掀了,气象局一阵惊慌,说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气功协会的主办人说:今儿见了个大世面。第二天,郑州市市长来到课堂上,恭敬地去和老师握手。据说他和他的儿媳妇来参加我们的班了。
接下来是济南的第二期。在济南体育馆,可容纳三、四千人,座无虚席。济南的这期班老师讲的非常细,以后要发生的一些事也告诉了大家。

下期班是大连,老师希望大家不要都去大连,大连是个死胡同,火车少,而且开班的票早已卖完了,并告诉大家30日那天不要乘飞机去大连。那次老师一路上受阻,魔干扰得很厉害,最后老师是从海上坐船去的。
记得在成都大连站长跟我说,她们和老师在一起照的像,上面有龙。我很惊奇,就说下次去大连给我看看好吗?她说行。这次去大连我惦记着这个事,就追着她要。有一天她给我带来了,我一看,真的,在她们和老师站着的后边天上,有两条龙一前一后挨着,头很大,鼻子眼睛的轮廓都很清晰,上面好像还坐着人。她又指给我,你看这是两付宝剑。我一看很小但清晰可辨,剑鞘和剑体是分开的。我愣愣地看了半天,她说只这一张,把底片拿去再洗,就洗不出来了。她的儿子说什么不相信,去实地考察了二十几次,最后只好作罢。后来第十堂课解答问题时,有个学员问,在看《法轮功》这本书时,看到了两付宝剑。老师说:是,我从宇宙中带来,威力无比的。
8月5日哈尔滨开班,地点在哈尔滨冰球场,那时冰球场还没建好,三面有座位,一面墙是三合板钉着。冰球场的工作人员从没听说过这么多人万里迢迢赶来参加的气功班,也跑来听课。有一天上课还早,老师走进来绕场看望大家,当走到学员前面时,看台上离老师近的这一面学员呼一下起立,虔诚地向老师表达敬意,老师向前走,前面的学员又呼的一下站起来,就这样随着老师绕场一周,学员们整齐地站起来坐下去,此起彼伏,这场面壮观极了,那一刻整个场充满了神圣与崇敬,连学员们自己也惊呆了,这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我旁边的一位第一次来听课的小声说:哎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什么国家领导人来都不可能。
延吉的一期在延吉体育馆,热心操办的是延吉最早出去听课的一位朝鲜族学员。他说他要给家乡父老做一件好事。据说他所在的单位70%的人都来听课了。那期最后一天,朝鲜族的学员穿上了鲜艳的民族盛装,五颜六色,这是他们最隆重的礼节,向老师表示感谢,为老师送行。课后有个简短的结束仪式,老师把收入的七千元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
那天从课堂上出来,我直奔火车站,乘图门江1号去长春,然后转道去哈尔滨。上期哈尔滨班时有位新学员借了单位的摄像机录了带子,答应做好后给我一套,当时这是非常珍贵的,那时都买不起摄像机,有录音机的都很少,我得赶紧去取。
一夜火车,清晨到长春,我把行李拖下来,很累。走到下地下通道口时停下来,立起箱子缓口气,一回头,见老师站在后边,慈祥地望着我,我又高兴又感动,又怕老师帮我提箱子(注﹕这与修炼界师徒关系的界定和修炼方式有关),慌忙说:“老师,您甭管我,您先走,我没事儿,我经常一个人上路,能行。”等老师前边走了,我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挪。我拉着箱子走到出站口,排着队出了站,一抬头,老师在前面站着等我出站,依然是那样慈祥地望着我,当时心里一股热流,真想给老师跪下,可周围人很多,老师身边还有学员,只好向老师合十,说:老师您别为我担心,我一个人能行。那天我顺利地到达哈尔滨,第二天奇迹般地回到了北京。
几个月后的12月21日,广州举办了第五期,这是在中国的最后一期。那时法轮功已经传播得很广,传得也很快,加上几个月没办班了,人们都翘首盼望着。又听说是最后一期,全国各地都有人赶来,东北、新疆,为了求道,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来早了,为了用仅有的钱维持听课期间的生活费,每天吃2元的伙食,在广州2元是吃不饱的,北京的学员拿出自己的钱来,送他们每人一百元。有一个东北的女孩,没有收入,大中型企业都停产了,她就去卖菜挣钱来听课,又用仅有的钱去帮助别人。还有兄弟俩背着铺盖,风餐露宿,几乎是要饭走来的。

(明慧网)
广州第五期据说来了五千多人,可能更多。广东省气功协会很早就把票卖完了,我的票是托广州的亲戚10月份买的,后来的学员就买不到票。第一天离上课时还早,体育馆前的广场就已人山人海,听说有500多人没有票,可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不允许超员,过道一律不准坐人。北京的部分学员把票让给了新学员,交票时,双方眼里含着热泪,边上的人也热泪盈眶。开课了,没有票的学员就守在体育馆门口的广场上。这样的锲而不舍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他们破例打开了旁边的一个馆,接了一个同步录像的电视机,让余下的学员进去听课。
广州第五期盛况空前,可以看到人们求法的心那样地迫切,众生的觉悟被启发出来,他们对师父的敬意也是任何语言无法形容的。有一天,学员很早就到了,在体育馆大门通往大厅的沿途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中间让开一条通道,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直等老师来。老师来了,大家簇拥着老师向老师表达敬意,大家从内心发出来的对老师的崇敬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他们问学员,你们老师是什么人?这场景从未见过,体育馆大场面不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样地虔诚。
广州第五期激动人心,大家明白了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也明白了自己要走的修炼的道路是怎么回事,都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我的小孩在美国留学,93年底回国参加了广州第三期学习班,回美后没能天天坚持,参加了广州第五期后,对她的震动非常大,回美后一人坚持天天炼功,还介绍给周围的人,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没能动摇她修炼的心。
广州第五期是李老师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学习班。以后的几年,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高潮,那次,美国、香港,还有欧洲一些国家都有人专程来听课,这些人回去后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在以后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弘传中都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回想八年来走过的路,万分庆幸自己赶到了大法洪传之时能亲身聆听老师讲法,亲受老师传功,这是令多少人羡慕的万分珍贵的机缘。虽然这多年吃了许多苦,遇到了许多难,但是这和以前无奈地受病痛的折磨时的心态已完全不一样了。通过自己吃苦修炼,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身上的脏东西一块块排掉,现在全身充满了活力,生命充满了希望,看到了广阔而美好的未来。其实生命原本是美好的,只是由于不知道宇宙的法理,在无知中造了不少业,就使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老师把宇宙的真法告诉了我们,又为我们清理了身体,下上了法轮和一切修炼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大法中修炼,身心不断地升华。不修炼的人会看到炼功人很苦,可炼功人会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是向上的生命,是能够与天地永恒的生命。过去觉得这只是人的美好愿望,而今天却真真切切身体力行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能跳出苦海返本归真了。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已经很长了。我想写出来并不是想表白什么,我是想说,师父的法传的太不容易,从开始传法这九年来,一分一秒都没停过。许许多多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他的品格的崇高伟大,他的智慧的浩瀚壮阔,用人的语言的内涵无法表达其万一。99年7月在大陆,看到电台、电视台疯狂地造谣,用它卑劣的用心把人不好的心都挑逗出来,世人不去说,有的炼功人也开始动摇,我就觉得这是多么荒唐的可怜,怎么能用人心去揣度佛心、用人理去评佛理呢。
在这法正乾坤的最后时刻,我回忆我走过的路,也把它讲给大家,是为了我们记住过去,不要自满,不要懒惰,一如既往地跟随师父前行,为了自己,更为了宇宙众生永恒的未来。
(2001年4月纽约法会发言稿)
文章中图片选自:
1. 法轮大法九年洪传纪实图片展──《正法之路》
2. 正邪是非,历史作证──“长春豪宅”的真象(图)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26/27760.html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张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