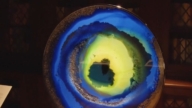按:如果发生粮荒会怎样?历史告诉我们的惨痛。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人浮肿到什么程度?就像将要作茧的蚕,体内蓄满了浆。水分从人的血管里肌肉组织里分离出来,整个人是透明发亮的。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时间: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点:纽约市贝瑞吉区
依娃:方晦先生,请先介绍您的个人简历。
张方晦:好,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到中学任教。母亲是律师,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学教师。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肃省阿克塞县。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务农。一九六四年,因常与几位同学在一起聚谈、同时开始文学写作(包括短篇小说描写三年饥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看守所关押长达八年多后,于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公判为无期徒刑。经过多次申诉,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曾任上海《萌芽》等报刊编辑。一九八七年出版长篇徐志摩传记小说《飞去的诗人》,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一九八九年来美,就读于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学。一九九七年以来出版长篇小说《美国,爸妈不知道的故事》和《这五十年》三部曲。
一家六口从上海“移民”阿克塞
依娃:我采访的目的,主要是想请你谈一谈你和家人在一九六○年大饥荒中的经历。
张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家庭先后遭受过三次大难。到了一九六○年,就巢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移民”大西北。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令把城市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统统清理到边远地区去,节省城市粮食。因为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
当时我们的家庭别无选择。父亲是一个体瘦多病、弱不禁风的知识份子,母亲曾经被捕判刑三年,年仅四十余岁,已中风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长子,只有十八岁,四个弟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离沪时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时只剩五、六件,说是翻车行李丢失了。
我们从上海同去的有大约五百多口人,一百多个家庭。最后落脚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南坝农场”。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几乎是与世隔绝。我们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窝子。甘肃移民局已经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个深坑,上面盖上红柳条和芦苇席当“屋顶”,这种洞穴一般是放骆驼的牧人的临时歇息之地,以躲避风沙和炎热,却成了我们这些流放者的长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应五百多人的大伙房开饭了,白面馒头,二两一个,没有定量随便吃,还有炖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喷喷的。大家彼此看看,觉得还不至于活不下去。
仅仅两天以后,伙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克扣就开始了。一顿馍馍,一顿玉米面糊糊。馍馍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刚开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粮,渐渐减到一天几两,吃饭就像吃人参。当时农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滩上连草都不长,哪来的瓜菜?加上干部的克扣,每天每个人能分到一点点羊肉,羊肉汤,戈壁滩上没有任何蔬菜。每个家庭每天必须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领得到饭。因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远,越来越难。往往翻山越岭走出好几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骆驼刺的根背回来,为了换到一点馍馍和玉米面糊糊。那里交通闭塞,火车站在几百里地之外的柳园,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搭车要“单位证明”,还要有粮票。所以,死活都离不开单位!
饥寒交迫 每天有七八人死掉
依娃:当时死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饥饿吗?死了人有人埋吗?有棺材吗?
张方晦:“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是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当不过了。到了八九月,晚上地窝子里就冻得人发抖,加上长期的饥饿以及高原反应,生病拉痢疾,上海来的人开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戈壁滩上有一种植物,大家叫它沙葱,吃起来很辣,有葱味,拿来充饥,一吃就呕吐腹泻,进而丧命。
初到时候,农场动员大家种胡萝卜,但是那里根本没有土壤,长不大,就被人连根带叶拔去吃了。还种过青稞,也是不行,颗粒无收。又没有水,大家上山挖水渠,每个人都十指磨烂流血,手肿得比馒头大。没有人敢于说一个“不”字。冬天来临了,伙房的饭越来越“水”,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被埋葬。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别人的人很可能过两天被别人抬出去。
最早死亡的是一对母子,女人三十多岁,儿子大概四五岁,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成天在住宿区跑来跑去玩耍。一天,他们居住的地窝子突然陷塌,一根梁木刚好打在那女人的头部,她当场死亡,那男娃子被刨出来时已经咽了气。农场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声大哭。
最初死去的几个人,农场当局做做样子,还用几副薄皮棺材,挖个坑把人埋掉。到后来,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来越多,就没有棺材了;那里连草席、被单都没有,把死人随便抬出去,浅浅挖一个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一些小孩一发烧一拉肚子很快就会死掉。单身的男人也特别容易死亡。移民中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划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业失恋的精神打击,劳动饥饿的肉体折磨,很快能把一个男人彻底击垮。女人相对坚韧一点。
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人浮肿到什么程度?就像将要作茧的蚕,体内蓄满了浆。水分从人的血管里肌肉组织里分离出来,整个人是透明发亮的。走路有气无力低眉垂眼,见了人也没有反应。农场里七八岁的小孩都会指着一个又干又瘦的人说:“这个伯伯只有两天了。”他们看得太多了,经验非常丰富,天数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来。
快饿死的人看起来非常恐怖,浮肿后又干瘦,整个脑袋只有拳头大,鼻子都没有了,陷下去了,只见两个黑鼻孔。两片嘴唇就像两片晒干的橘子皮,牙床骨暴凸出来,胳膊腿就是皮包骨头,麻杆子一样。一个个大男人就这样死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
短短半年时间,到一九六一年春天,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了百分之四十。
人变成动物 女人变成妓女
依娃:在那样饥饿的情况下,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张方晦:因为饥饿,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会扭曲变态到极点。每一个家庭都有难以置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一个教书的女同事,二十多岁。我去她家亲眼看见,他们打回来一锅面片汤,为了平均分给一家三人吃,要先搅拌几十下,然后飞快的分成三份,否则分不匀。一家人,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农场供应的玉米,都是整粒的,就煮熟了来吃。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来还是玉米粒。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孩蹲着拉大便的时候,另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玉米粒就往嘴里送。
伙房仓库里有胡萝卜土豆玉米等,晚上就有人掘墙凿洞,钻进去偷吃。被积极分子发现举报,这些人就被捆绑送到阿克塞公安局,不几天就听说被抓的人已死。还有一些胆子大的人破口大骂:“政府是大骗子,欺骗我们来到这个鬼地方,就是要我们饿死冻死,让我们自生自灭,是杀人不见血。”这些人也被抓起来,不久就都死了,没有下落。而农场干部管理人员私吞职工的口粮,他们个个体壮如牛。
如果在那时你看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瘦,一点都不憔悴,那么她一定是和哪个干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绿帽子,不会打骂、不会阻拦。因为这个女人总能带回来一些馒头一些吃的,能让丈夫和孩子吃饱一顿。其中有一个女人,三十几岁,颇有姿色,有三个孩子,她都得养活呀。在人人顿顿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女人能吃饱,吃得好一点,就看上去特别漂亮。农场的干部驻军的干部,无论白天晚上随时传唤,这个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强迫,因为撕去了羞耻的面皮后,她能换得吃饱肚子,养活丈夫孩子,还有性的享受,因为那些光顾她的干部肯定比她老公强壮得多。她就成了一个妓女,用身体换取食物。有人骂她“破鞋、不要脸、婊子”,她就马上报告,骂她的人就要遭到惩罚。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女学生,才貌出众,可谓沉鱼落雁,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家,娇生惯养长大,到那里后变成一个公共情妇,什么教育局长交通局长都能找她睡觉,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温饱为了生存而已。
这时移民中就会有“霸头”出现。其中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拐子,很厉害,谁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诱上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上海女孩,就因为他能够给女孩家一点他从伙房里弄来的粮食,对女孩家人来说算是救命恩人了。后来他又生妙计,将这个女孩嫁给一个从甘肃武威县“移民”来的老乡青年,换得一整只羊,还有两百多斤面粉。以这个女孩“干爹”的身份做成一笔大买卖。一九六二年,农场解散,我们这批没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归,这个人又唆使那女孩从丈夫身边逃出来跟着自己一起回到了上海。
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像是一只在戈壁滩觅食的狼
阿克塞气候恶劣,春秋飞沙走石,高原紫外线强烈。来自上海的女性们,刚来时脸蛋还白嫩水灵,不出半年,先是红,后是黑,然后皮肤发硬,结成一层厚厚的痂,像壳子一样。我两个弟弟的脸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着划手。
食堂吃不饱,肚子整天饥肠辘辘。我和十三岁的弟弟,用家里的被子、单子、毛毯、钢笔、衣服、小镜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较远的牧区和当地哈萨克人换羊肉换青稞粉。其中还有野羊肉、大头羊肉,一床被子能换来十几斤肉,够一家老小好好吃几顿。就是金属匙羹,不锈钢厨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萨克人见了也很稀罕,样样都要。换来的肉有新鲜的也有肉干,有时还有整块的羊油。羊油特别坚硬,吃面片汤吃青稞糊的时候,切下来一些,拌在碗里,以增加营养和热量,让一家人苟延残喘维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运地换到一个旱獭,背回来特别兴奋,剥皮开膛,什么都舍不得扔掉,肠子肚子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煮了一大锅,全家人美餐一顿,其肉其汤都鲜美无比今生难忘。
虽然我才十八九岁,却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亲来阿克塞时就是被人用担架抬着下卡车的,母亲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来,最关心的是我手里肩膀上有没有什么吃的。有时我一个人东奔西跑,就像一只戈壁滩上寻找食物的狼。食堂里的饭没有一天能让人吃饱,偶然不饿的时候,是我从哈萨克人那里换回来一条羊腿,一锅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饱餐一顿再说。
一九六一年,当局将我们转移到甘肃安西县踏实农场,那是个老农场,已经有两百多上海移民在那里生产生活。我们最初去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叶子,我父亲的状况好转一些了,能下床,能扶着墙慢慢走路。母亲也得劳动换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编筐子,大弟弟也跟着母亲一起编筐。
“踏实农场”一百来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读书,虽然名义上有个“职工子弟小学”,但管理学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学校而无学生。他们成天提着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当时也能卖一点钱补贴家用。小女孩,十五六岁就急着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饭吃了,是条出路。当时最抢手最吃香的是司机,因为有车到处跑,总能拿回吃的用的。嫁给一个司机,全家人都能跟着沾光吃饱。
长期的饥饿,让许多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营养不良、贫血、肝肿大、胃病,浮肿、黄瘦等。女性们几乎全部停经,当时叫做“干血痨”。根本没有女人生孩子。全农场只有一个新生儿,是从上海来时就已怀上的,那个小姑娘长到两岁,双腿还是软软的,绝对无法站立。
我们到达“安南坝农场”后不久,我看到一份过期旧报,说全国大学将招生不足,《人民日报》要求各地“千方百计发掘考生来源”。我就试试到场部找书记请他允许我报考大学。书记一听哈哈大笑,以为我在痴人说梦。“你这个张老师,我实话跟你说,你来这里了,一辈子哪里都不要想去了,就在这待着吧。”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局移民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
写出大饥荒小说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么会看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张方晦: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一九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
我是几乎被迫害漩涡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的农民,因走投无路,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海门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依娃:你这样写,意识到危险性吗?
张方晦: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这些年,我时时刻刻都在绝望之中,时时刻刻都感到会被处死逼死。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经长出过很多淋巴结核的肿瘤,也曾大量便血,人干瘦得皮包骨头,几度挣扎在死亡线上。
但是我不后悔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我长期想不通的是:全国那么多大科学家大作家大学者,从一九四九年开始,都一直歌功颂德、紧跟当局,违心地指鹿为马,怎么会看不出我一个十八岁高中生凭直觉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大跃进放卫星,那样离谱,怎么没人看出是虚假欺骗?
五十年过去了,直至今日,我还时常会在睡梦中忽然惊醒,突然看到一个饿死的人的脸,那种神魂不宁的痛苦对谁去说?中国历史几千年,有哪一个暴君哪一个昏君曾经草菅人命到这种地步?丧失人性到这种程度?
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读过一本书,是苏联马戏驯兽专家杜罗夫写的《我的会演戏的鸟兽》,说他训练动物的一个诀窍就是不给它们吃饱,那样它们就会百依百顺地听从指挥;在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动作后,才给一点食物,但仍不让它们吃饱,它们才会永远俯首贴耳顺从如奴──那个时代的农民,还不如驯兽师笼子里的鸟兽。
那段历史不能忘记,值得留下真实的文字,让我们的子孙后人牢牢记住,以史为鉴。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