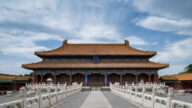关于鲁迅,数十年来的研究之作可谓多矣,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恐不为过,实际上早已成为“鲁学”了。
而鲁迅之“骂人”也早已闻名海内外了,尽管其大呼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却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骂遍了整个中国文坛,并波及到科技界、梨园界与武林界。
诚然,在历史上,鲁迅用他那枝泼辣犀利的笔,骂了许多该骂的人和事,不愤怒安可!
然而(请原谅我用了鲁迅喜欢用的转折语),鲁迅也骂了不少不该骂的人和事,由于他的多疑、偏见、偏激和冷嘲热讽,不仅制造了不少“话语暴力”,而且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了一些人。
否定京剧 对名人进行人身攻击

比如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京剧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并对有人把他和梅兰芳“并为一谈”,看作是极大的侮辱,愤怒异常,进而对梅兰芳予以人身攻击,在书信中以不屑和亵渎的口吻称梅兰芳为“‘梅郎’之流耳”;并断言梅兰芳的光芒将很快在中国暗淡下去(抗日时期,梅兰芳蓄须拒演,表现出可敬的民族气节。对此,丰子恺表示衷心敬仰。在其死后,还一再撰文追悼)。
鲁迅对另一位既无私交也无私怨的马寅初,也发出了“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之言(《两地书》),并在《拟豫言》中对马寅初予以了讽刺,所谓“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云云。其他如在《故事新编》中,用口吃和红鼻子来嘲笑和影射有生理缺陷的史学家顾颉刚等,则是尽人皆知。
鲁迅还在文章中骂民国文人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写的。
邵氏后对狱友贾植芳说: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见2006年第10期《读书》)。故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26年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中载文说,鲁迅“……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云云。
鲁迅自己也曾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说:“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曾倾倒于西方尼采“超人”学说的鲁迅,在师承被革命党的《民立报》称为“章疯子”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后,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而章太炎早在同盟会时就以“骂人”闻名。
有其师必有其徒。鲁迅曾夫子自道云:“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不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骂”(《鲁迅全集・书信・致吕蕴儒》)。
对人如此,对事也不例外。
妄自尊大 乱批中华传统中医
众所周知,鲁迅早年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时并未毕业(顺便说一下,鲁迅所敬重的藤野先生之所以对其热情和认真的辅导,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汉文化的热爱与崇敬),故而以他那有限的一点西医知识来评判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不客气地说,实在是“蚍蜉撼大树”。
也许捷克著名作家齐米茨基在文学成就上不如鲁迅,但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上,这位在法国获得了医学博士、并担任过心理医疗中心主任的作家兼医学家,却很仰慕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对中国的中医情有独钟。
他曾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中医和针灸,他意识到,同中国古老的医学相比,西方医学有一个很大的劣势:过多使用药物。
针灸则不是这样,只是刺激能促使肌体和谐的穴位,而借助这种疗法能够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见2006年5月25日的《参考消息》)。
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教授、诺贝尔医学奖评委秘书汉斯・乔尼瓦勒认为,武断地说西医是科学、中医不是科学,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科学。
为什么要取消中医呢?
现在西方社会正在开始正确地认识中医,诞生中医的国家却要取消中医,这可是件让人忧虑的事情!
在应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时,我们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及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副作用的药品。
对于某种治疗方法,不管它建立在哪种医学理论基础上(瑞典著名血液学专家比格.布洛姆巴克博士认为,中医和西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医把人体看作是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的组合;而西医则认为,人体是由各种器官、血管、神经中枢等合作形成的),治愈病症才是其最终目的。
英国中西医兼治医生菲利浦・费农,则对鲁迅的忠实信徒张功耀于2006年10月7日发起的“取消中医”活动感慨道:
“很多西方人不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一些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也接受了西方人的观念,否认中医药的价值。这中间也不排除西药公司的背后利益在起作用。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应该珍惜它。”
笔者以为,毛泽东与鲁迅在“与人斗”上是心灵相通的,故而“斗”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然而在今天,失去宽容心的彼此相互之“斗”,将带来社会和世界永无宁日之“乱”!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