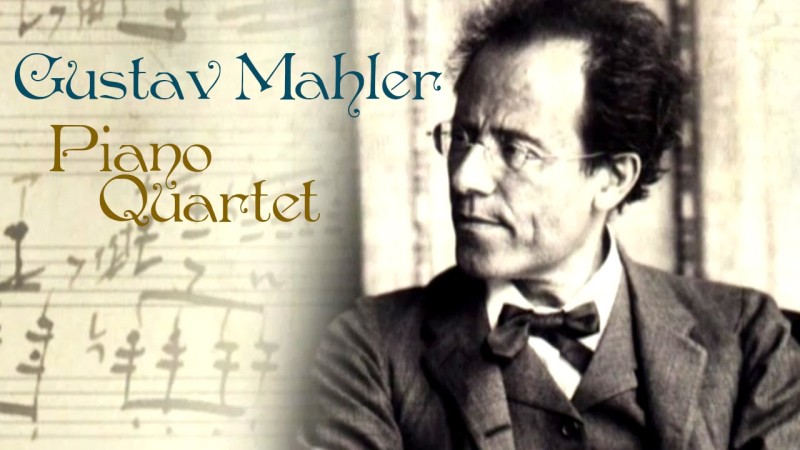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在这一段听马勒的交响乐,以及对于音乐及文化的思索和探究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越听得多、看得多,我就越觉得自己依然不很理解西方音乐及西方文化,为此也就越来越不敢多说了。为此,写下的文字不过是分享我的困惑。
在我最近两三年的思想研究中,尤其是对于政教分离、十九世纪后的后基督教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我在多处谈到关于Romantik,浪漫派的看法,其中特别谈到它的中文翻译,“浪漫的”、“浪漫主义”问题。我认为,中文把Romantik翻译成“浪漫主义”严重地,导了人们对这个术语及思想文化倾向的理解。在我看来,大约翻译成滥漫或者滥蛮主义倒是更为恰当一些。因为它是在描述一种主观意念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但是现在,在经历了这一段听马勒的音乐,对马勒音乐的体会及探究后,这个Romantik究竟在十九世纪,在欧洲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地位影响是什么,通过听马勒音乐及对于不同作曲家及指挥家的认识,非但没有让我更为清晰,反而让我越来越感到困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定位及描述它,不知道我是离西方音乐越来越远了,还是现在才有点入门了?
在对它的了解中,以交响乐为例,它几乎可以说是和Romantik一起发生展开的形式。它不过是发生于巴赫的宗教音乐之后,经过海顿、莫扎特的所谓古典音乐形式到贝多芬才开始展开的形式,及至到了马勒,才可以说它的规模及形式较为成熟,但是却立即就变得有些不可收拾。并且就在此嘎然而止,转向了现代音乐。这时间不过几十年,它几乎亦步亦趋地伴随着政教分离的社会文化潮流发生、发展。而有意思的是,第一,这个过程竟然几乎完全是和中国京剧的发生、发展时间同期。
第二,注意到上述这点,在阅读马勒时就让我进一步发现,同期的西方歌剧及演员、剧目等在剧院及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也几乎和京剧等戏曲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相同。而交响乐不过是歌剧,这个西方“戏曲”的序曲和间奏曲发展出来的形式。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国人不必那么神化西方的交响乐和歌剧,它不是永恒的令人眩晕的神庙,而不过是和京剧一样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也是刚刚走出幼稚就拐了弯,步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妄自菲薄会败坏你的审美口味及能力。
为此,第三,了解了这个过程让我更加理解,西方人对于京剧的惊叹和佩服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对于文化及艺术的理解深处的。因为他们的歌剧除了音乐外,表演艺术实际上是非常粗糙,这个粗糙保持到了今天。他们的歌剧的辉煌在于布景和外置的设置。而演员的表演始终没有进入人文的场景——中国人的所谓艺术的修养中。
我之所以说到这个歌剧,是因为那个Romantik,即滥蛮主义实际上是音乐受歌剧、文学、诗歌,乃至各种社会性的观念的影响的产物。Romantik,不是纯艺术的追求结果,而是一种世俗化的人的冲动的产物。Romantik的艺术追求的不再是精神——超越的宗教性的精神,而是人的物化及欲化。它不折不扣地是人的观念化的产物。所以我实实在在地开始怀疑,贝多芬的Romantik和十八世纪末期后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类似的倾向及性质,从而在一些方面是和其后,即今天的物质化、人的欲望的无休止的膨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而马勒则却是因为感到了这种倾向,而产生了困惑及痛苦。
在这意义上,在听马勒音乐的时候,我感到,马勒的音乐可以说是比贝多芬带有更多的精神内容,并且努力试图重新向精神音乐回复。
这些被常人看来奇怪的问题,既让我诧异,也让我不安。这也包括一位朋友问我,托斯卡尼尼指挥过马勒的交响乐吗?托斯卡尼尼是如何看马勒,如何诠释马勒音乐的?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更加感到我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陌生。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打开了我另外一扇好奇的窗户。事实上正是托斯卡尼尼到纽约后取代了马勒的位置,并且把马勒从纽约交响乐团挤走的。在对于音乐的理解和处理上,他和马勒也完全是两个倾向。
作为指挥及对音乐诠释的理解,托斯卡尼尼极为反感马勒及德国的Romantik传统。他认为要对音乐的理解要回到乐符及音乐本身,不能够随意按照主观的理解诠释修改。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在对音乐的态度上,这和我们一向的教条性的理解相反,这位意大利人要的是音乐的客观性,而反对德国人的Romantik,滥蛮性,随意地发挥诠释。流俗的观点认为德奥传统严格、拘泥,意大利人天性热情、活跃,不拘一格。可在这儿居然完全是相反的。对我来说,矛盾的还有,如前所述,照我的理解,马勒及其音乐是对Romantik,滥蛮主义的反弹的产物。可几乎所有的乐评都把他作为最后一位Romantik,滥蛮主义的作曲家。为此,这就让我的思想陷入混乱和苦恼,不知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不知究竟如何定位,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为此,它也就再次让我回到了前面的问题,Romantik,滥蛮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十八世纪末期发生,十九世纪末期式微的倾向究竟是什么——它和德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在巴赫之后的交响乐除经过所谓古典主义立即进入滥蛮主义外,还有别的发展的道路及可能吗?近代发生的交响乐可以说是滥蛮主义的结果吗?或者说它一直挣扎于滥蛮的暴力影响下?而时下,难道滥蛮主义过去了,为此交响乐的时代也就过去了?难道以巴赫为代表的音乐中的精神是被贝多芬们结束的?
我真的是越来越糊涂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最近二百年中发生的,世界的变化不仅太快,而且太粗糙了!被人们惊叹的辉煌,实际上人们从没有仔细地观看过它,细致地加工过它,充分地消化过它,研究过它。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根本不给你这种细嚼慢咽的可能。毁灭的速度难道不是比建设的速度快上千百倍?
所有这一切,我大约还是必须要回到文艺复兴、启蒙思想、政教分离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变化中去寻找。这也就是说世俗化、人本化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我问的不仅是它给欧洲,而且更是它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古往今来到今天为止,这种文化,也只有这种文化具有能力并且已经席卷了人类存在的所有地方,摧毁了所有其它文化。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还来不及思索就已经掉入深渊。这一点突然让我看到,半个多世纪前物理学家提出的黑洞学说,这个理论不仅存在于人类对宇宙的理解,而且也适用于对人类文化宇宙的认识,为此,它可能是一种对人类的反讽。
我们在试图理解宇宙黑洞时,却没有发现还有一个文化黑洞,我们在还没有遇到宇宙黑洞之前,却已经落入了文化黑洞……!
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来模拟理解文化,那么描述西方文化的方程也有一个奇点。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个二元的文化的分母已经显示出了这个奇点:因为在历史上,基督教导致的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及社会,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在现实中,没了基督教,即政教分离、基督教退出后的时期,它却或者是导致世俗的政教合一——极权主义,或者是无尽的政治上的排他、悖谬和冲突,如最近二十年世界所发生的问题,它让我们看到一百年前,以及今天,我们都在直接并且激烈地面临这些问题带来的灾难及压力。
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个文化的分母等于零,这二百年的历史似乎应该对此是有答案的。音乐的探索或许比思想的探索更为敏感和直接。你觉得炫目、辉煌无比的东西,马勒们觉得它粗陋、问题重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勒的努力可能是在解答在音乐上出现了奇点的麦克斯韦尔方程,他告诉我们,它的协变需要新的假说,即新的形而上学前提。我们现在才感到并且经受的黑暗和灾难,可马勒早就感觉到,并且在寻找出路。
这一百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普世的人权和普适的民主价值如同光速不变那样,是文化问题的电磁方程协变的前提!对马勒来说,它导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导致自然万物、生命之间的联系,那个在东方早就存在的假说。
在这个意义上,马勒甚至又是走到了当代物理学家的前面。因为现代物理学家提出黑洞假说,从“无”中理解宇宙,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之路,是在马勒去世后很久的事了。
在这个东西方的问题上,当你觉得西方及现代化,包括交响乐是一座神庙的时候——因为你见到它就已经在膜拜它。所以你就是经历了灾难,牺牲掉了生命,因为你俯首、叩头、闭目,你什么都看不到。可当你和西方人一样上了船,你看到和经历的是茫茫大海,是风浪,你就会觉得船上的一切,海上的一切都是问题,稍不注意,船就会被狂风险浪打翻。而最严重的是甚至注意了可能也没用,因为制造这艘船的材料和工艺可能先天地存在问题,那材料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脆裂、溶化,也可能因为海洋、宇宙太浩瀚难以预料了!
我们真的很无辜,本来是可以不上这条船,或者像日本人一样穿着自己的救生衣,可我们主动上船,主动粉碎了传统——这道抵御危难的衣物,比船上的西方人还赤身裸体,所以我们的灾难不仅自找,而且一定会更为严重。
听马勒的音乐,听另外一种宇宙神韵,生命联系的呼唤,也许能让你感到亡羊补牢、重新回归,为时未晚……!
2017-6-19 德国·埃森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