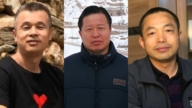中国是人类权利的洪荒地带,整个国家的历史,乃至它的哲学领域、社会伦理思想领域,个体权利从未成为一种被注意的对象。它实际上没被当作一种具体的存在而有意识地对待过。而有意识地压制、消灭个体人的权利、消灭部分人已生出的权利意识则是过去68年里制度永不倦怠的意志。
先是以一切恐怖的手段压制,消灭客观的权利行为,后是彻底消灭与权利有关的思想。权利作为一种行为现象几被根绝,权利思想或叫意识实际亦被消灭殆尽。面对赤裸裸的,有时是极其野蛮的滥权行为,人们习惯于逆来顺受,长此以往,完全混淆、颠倒了正当与非正当、合法与非法的本来。导致了滥权的更加肆无忌惮。
权力如何行动,其核心的积极的监督和规制对象恰恰是公民自己的保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及积极的行动。行政、司法的监督则是消极的,间接的和被动的。这两种监督或叫救济行为依然是要以公民的积极告申为前提。一般情况下,公民若不积极告申,后者监督或救济功能则更是形同无物。
所有人类的经验普遍地表明,权力失去监督便会走向毁灭,但在它终于毁灭前的邪恶及祸害的恐怖是罄竹难书的。一味地诅咒黑暗而忘了自己作为个体对社会、说白了就是对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这实在的是个不可饶恕的罪错。我个人有过多次这方面的经历证明了我判断的意义——抗争、保卫自己权利的意义。
我在列车上从未接受过身份证检查。每次坐列车,百分之百在卧铺车厢里会要求出示身份证供警察逐一登记。我百分之百绝不配合,其实身份证就在我身上。我每次都直接说自己不同意出示身份证件,无疑大都会出现进一步的纠缠情节,但结果他们必败无疑。道理很简单,乘坐火车只是我与承运方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行为,与任何第三方不发生关系。除非我实施了必须与第三方发生关系的法律关系行为。
我从未见到过类似情形下其他人拒绝的行为,相反,有时这种过程中警察会坚韧不弃,不特如此,还会呼来一大群同类旁助,场面宏大则气氛紧张。对我的坚决不从,不少其他乘客会加入劝说大阵,我更具坚韧精神——绝不妥协,迄今他们从未得逞过。有时会有些乘客阴阳怪气地问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当然有,我只要不违法,我作我自己的主,我就是我的绝对统治者,任何人无权侵蚀属于我自己的权利。
一次在新疆南疆的一个县城,我乘坐的大巴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共匪特警拦下,车刚停稳,匪警蹬车大喊全部下车接受检查,那种跋扈使人感到一种无理的羞辱。
我是全车唯一拒绝下车者,这显然是不得了的大事——于蛮横惯了的他们。一位头目与另一位特警上来问我怎么回事?想干什么?我未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一字一顿告诉了他们从停车至实施检查过程的程序违法之处,指出迄止现在我依然不清楚你们是警是匪?指出平端枪口对人是违反行政规则的。结果他们不屑地互视了一下后,那头目突然说,请我下车帮他们训练一下他们的特警,教练大家如何端枪。我盯着他的眼说:“如果你是匪徒,我就开始夺枪,如果你是公职人员,我却没有训练你们的义务,但却有批评监督你们的权利。”双方沉默对视足有一分钟,结果那头目轻扬了下巴后,几人默默地下了车。
我是那天50多人中唯一没有接受搜身检查的人。当然这种结局在共匪治下的中国是极具偶然性的。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张长江律师遭遇到的情形恐怕换了谁亦例外不了。
张律师儒雅风度不凡,2002年的一个晚上12点时驾着豪车回家。北京还实在的是个典型的北方城市,一到晚上12点钟后街上道上几无行人,除了疾驰的车辆。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他的车被一群大盖帽拦下,说要检查身份证,出于律师的习惯意识,张律师要求对方出示公职人员身份证件,不料这冒犯了这群匪徒的变态权威心理。权威立即兑换成了流氓行径,他们掏出了枪耍开了流氓,用枪指着这位文雅气质满溢的律师,说这东西可以证明身份了吧?
第二天上午办公室一见面他讲述这一过程时,说彼时他感到震惊不已,说毕竟这里是首都北京,人际身份水深莫测,他们就敢公然在大街上这么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述完一脸困惑地问我:“高律师你说他们怎么会这样?”
于我而言,我从不虑及过多,依然坚持我自己应当坚持的,这种坚持多不胜数。有一次我开车在东三环三元桥下被拦下,警察过来就一句“好家伙,不知道单双号限行的规定吗?今天限制双号车上路,你怎么开着双号车满世界跑?”“没有人告知我”,我回答。“嚯,北京晚报天天公告,您干嘛去了?”对方来了一句。“看报纸不是公民的强制义务,我从不看报纸。”我说。“您还给我说这个,北京市政府下达的命令,我们只是执行者,您接受处罚吧”,对方显得很不耐烦。“我在合法行使我的财产所有权,凡涉及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规范只能由基本法律来调整,《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得很清楚,你不是在执行,而是在破坏法律秩序。”我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他们最后亦不了了之。
我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历,实在是想使人们知道,只要你理直气壮地坚持,不用害怕失败,必须使滥权行为碰壁,至少使他们觉得不易随心所欲。我在北京期间,除了停车被像鬼一样偷着贴上罚单,当面的处罚他们从未成功过。
一次,我在新华门至天安门间红绿前被拦下,一下车未告知我任何程序权利便劈头一句:“驾驶证、行车证交来。”“没有驾照”,我回答(我是辽宁省驾照,正适一年一度审照之际)。“你没有驾照怎么开车?”对方显得很惊讶。“你亲眼看到了我会开车的事实,这事实正是你想处罚我的基础”,我说。“行车证拿来”,彼伸手说。“没有行车证”,我又说。“没有行车证怎么证明这车是你的?”他更显吃惊地问。“你亲眼看到我是本车的控制者,且并无旁人对此控制提出异议”,我说。“什么外国情理?走,到马路对面接受处罚,扣车,人留滞说清问题。”彼说完便借着绿灯昂首过了马路,待过了马路才发现我没有跟在其身后便向我招手。我并不理他,等下一个绿灯亮起,彼跑了过来,我正拿着笔在纸上记录他所有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的情节,总共有六个方面的程序硬伤。
我就这么认真,我并不是想逃避接受处罚。你在其它过程中怎么恣肆滥权我没有力量管,但你处罚我即必须是合法处罚,否则处罚完就去起诉你。所有情况下,都是最后一脸不耐烦地挥手让你“走走走,不处罚你还不行吗?”放弃职责虽是他的事,我依然会提醒他们,不处罚更是违法的,与此同时,他们几乎是推着让你上车走人。
我在北京一家房管所办理房产证的荒谬遭遇值得一提。我清醒地知道面对这种野蛮无人性的制度,个人一已之力的较真是没有多少实质性价值的——除非大家都这么做,但在具体的办事环节上,我要的实质性的价值就是达到把事办成的目的。依着他们的规定本当顺理成章成就的事,却每必得采取令人屈辱、有失尊严的非常手段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你面对的就是一群无赖。
我去房管所办理房产手续,你具体的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为公民办理房产文件,可他偏就不给你办。我排在第四位,队排了很长,更长的是等待时间。不高的柜台那边,几位公务大爷在那里高跷着腿目空一切地海侃着。每一位递过去的材料都遭了一把被推开的命运:“明天来。”里面那位公务大爷语气干脆、不容置疑。排在我前面的三位碰壁者都铁青着脸旁立在不大的大厅里。
我一直在心里快速地盘算如何对付这“公仆”泼皮。终于临到了我,躲是躲不开了,我一手托着柜台面猛地一跃跳进柜台里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扑过去抓住他的胸依居高临下把他压制在椅子上。彼大惊失色,语无伦次,明显地有些恐慌,不断地也是本能地挣扎着,口里重复着:“你干嘛?你干嘛?”我说,“我是来解放你的。你的领导都是一群冷血的畜生,把你安置在让你如此痛苦的位置上”,我盯着彼说。“你骂我们领导,你骂我们领导”,彼像抓住了一丝救命索似的。我一把拉他起来,“走,一起去骂你的王八蛋领导去。”不料他突然猛地挣脱了我的手,一跃跳出柜台,发疯似地从那些刚才被他拒绝但还没离开的人手里抢过了手续,嘴里不停地嚷嚷:“我这就给大伙儿赶紧办还不成吗?”进了柜台后一边办理一边还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虽然经历了些波折,但那天我实现了办事的目的。人们常说共产党政权是流氓,这实际上是矮化了流氓的标准。第二周我又去那里取办理好的房产证,他一眼看见排在队列中的我,热情招手,嘴里竟说:“您不用排队,您怎么能排队?”“你连醒来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回了一句。
人是很难要求一律的。对别人的苦难、不如意无动于衷已是使人失望的事了,尚连保卫自己正当利益的冲动都不再有,你期待这个社会好起来,这无异于期望雄鸡去下蛋。只有自己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整个社会重视个体权利的局面才会实现,每个个体均不当贪得份外利益,把期望冀于别人,至少当绝不含糊地保卫自己的正当利益。
社会安全的载体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每个个体便是社会这张大网上的一个具体的绾结,你的放弃便导致一个现实的漏洞,这是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正是我们作为个体的无底线迁就、放弃,公共权力才会生成长着一个狰狞面目的冷酷怪物。而绝大多数逆来顺受的情形下,极个别人的抗争也就常作了牺牲的材料,于大环境的改变犹一箭入海之效。
相关链接: 附: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下载 (点击这里)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