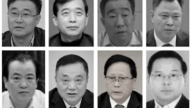长久以来,不少中国人一提到“法轮功”,就会首当其冲地给其扣上“搞政治”的大帽子。虽说这顶帽子继承的是文革遗风,然而,真正恶意转嫁给“法轮功”,则应该从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前后算起。
有了这顶帽子,1999年正式实施迫害前夕——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就“天津公安无理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事到北京和平上访,被顺理成章地说成了“搞政治”;此后2004年,法轮功为揭露中共暴政以及无辜蒙冤的真相而刊发《九评共产党》一书也被中共气急败坏地指为“搞政治”;再以后,在长达十几年的岁月中,法轮功学员为唤醒良知、坚守正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向身边的有缘人揭露迫害、讲述真相的义举,也时常被那些受谎言蒙蔽的人说成是“搞政治”;直到今时今日,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大形势下,20万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最高法院投递了“诉江”状的合法行为,仍被一众追随江氏集团的公、检、法人员认定是“搞政治”。
还有不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好心人”,他们很愿意将法轮功的修炼者与宗教的修行者等同起来,口口声声地劝说着,“你们觉得好,关起门在家练就行了,何必到处跟人说政府不好、共产党不好?你们不要搞政治……”,那意思是,人家和尚、道士一般都在寺庙、道观里远离尘世的清修;本该“不问世事”的修行者怎么会有政治上的诉求?又如何能对国家的政治情况、政府的执政行为感兴趣?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入德国纳粹时期,一位主张“与政权对立”的宗教社会主义者的自白。他在面对“国家公权力变得粗暴无情”时表示,“一个新教教会若向纳粹主义敞开胸襟,……,就会再度背叛她对世界的使命”;“‘上帝的国不在世界上’听起来似乎很顺服上帝,显示的却是……顺服获胜的政权及其魔力”。这番话能给人带来的思考是,基督徒到底该顺服于上帝,还是顺服于政权?
我们不禁要问,“顺服于上帝”与“顺服于政权”相矛盾吗?处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致力于“非宗教的基督信仰”的神学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当基督徒被压迫在纳粹的世界观下,被强迫接受反犹太主义、被逼着仇恨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能以基督‘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诫命,与之相对抗”。而在具体的行动上,这位神学家所在的教会也做出了“控告纳粹国家损害人权”的义举。
在他看来,本该“顺服于上帝”的教会“没有权力将国家的力量占为己有”,“但是,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可置身于政治之外”。同时,他还向那些“对国家如何执行职权根本不感兴趣”的基督徒呼吁,“你们要努力尽一切该尽的责任”,“对于世上的一切,我们不能放任自流,我们的信仰不是鸦片(让我们在不公义的世界里感到满足);反之,正因为我们努力在尽世上所有的责任,我们才会目标更确切的坚持提出抗议”。
从这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宣言中,我们显然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存在于俗世的任何宗教或信仰团体,他们不该是一群“爱做白日梦或踩在云端的人”,而是一群无心于权力,却对强权、暴政侵犯人权、滥杀无辜的恶行奋力抵抗的人。他们不仅要求自己从生命的根本弃恶从善,更要全身心地去承担、完成伐恶扬善的使命。
若套用在修炼者与政府、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面对中共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关,实施了数次令世界震惊的大屠杀,如今又高举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大旗、残酷迫害法轮功信仰人士的人权灾难,对于一个真正秉承良知、坚守信仰的修炼者而言,只有站出来揭露暴政、制止邪恶,才能被视为是“正信”所往、“大善”所在。
其实,法轮功并不像人们所认知的宗教那般,拥有着一系列繁冗的管理形式以及早已被世俗化的宗教仪式。这些修炼者坚守着“不建庙宇、不收钱财”的原则,更不会对拥有政治权力有所期待。即便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一旦明白了“权力与责任不过是一柄双刃剑”时,也会在投身于国家权力之前有所迟疑、深感负重的。因为拥有权力之后的责任恰恰在于,要时刻限制权力,并将更多的权利还赋予人民。这也恰恰是普世所要遵循的,连宗教人士、修炼者都不得破坏、需要谨守的人权价值。
常言道,救人于水火、救人于危难,善莫大焉。当法轮功学员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抓捕、关押,受到非人的折磨与虐杀;当他们深知,中共暴政下的中国人正以无数直接或间接对生命产生危害的方式,不自知的遭受迫害时,告诫、劝说,揭露谎言、讲清真相,不正是一种践行“大善”的救人之举吗?就算是“抗议”,那也是一种最和平、最无声、最善意的抗议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