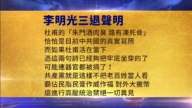一
我的父亲1933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朝中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说我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活下来九个。我父亲排行老二,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他自然从小就有了帮忙养家的责任。
我记事后,是到了高中时代,也即1980年代,才第一次跟随父母回到朝中老家。几位叔叔仍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土墙屋中,家中真正是“家徒四壁”,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也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只能用昏暗的煤油灯勉强照明。
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完全是赤贫的家庭,1949年“土改”划分“成分”时却被划成“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这个词,是我1973年上小学一年级,填档案表被要求填写父亲的“家庭成分”时第一次听说的。那时人人都有个人档案,从上小学起就跟着你,跟你一辈子。刚上小学的我已经知道了有“地主”、有“贫下中农”,却不理解什么叫“小土地出租”。问妈妈,她立即愤愤不平地说:“你爸爸家人口那么多,地并不算多,要按人均土地面积算,挺多划个‘中农’。吃亏就吃亏在雇了外人帮忙种地,结果就划成‘小土地出租’了,划高了!”

1990年代,作者再次回到老家,土墙屋依然是旧时模样。(作者提供)
我听的似懂非懂,但隐隐的明白,“成分高”是件很可怕的事。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因为爷爷是地主,全班同学都鄙视她。我有一次到她家,无意中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黑棉袄、坐在角落没有出声的老头。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她的地主爷爷,心中立刻觉得非常恐惧,像看见妖怪一样,找了个借口赶快逃走了。
还好我母亲的成分是“城市贫民”,算是无产阶级,将父亲的“高成分”“扯平”了一些。
母亲的生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她被送给了养父母。其实,母亲的养父,也就是我外公,曾是个“资本家”,在中江县城拥有一个酿造厂,一个门市部,我父亲就是在外公的门市部当小伙计时认识我母亲的。后来外公抽鸦片,家道败落了,因此到了共产党来了划成分时,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据说外公后来经常在外婆和母亲前夸耀自己抽鸦片的功劳:“要不是我,你们能沾光当上‘无产阶级’?”
二
父亲小时候念过一点私塾,后来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每天自己背着干粮当午饭,作业必须在学校做完,回家后所有的时间都得用来帮家里干活。每一个“场”,他还要编出一“个”布去卖。
四川人把去集市叫作“赶场”,农村似乎是十天半月就赶一次场。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一个布”到底是多少,小时候没问过父亲。
父亲十几岁时,执意要去县城读书。奶奶不想让他去,因为家里需要他,所以就给他说了一门亲,想让他早点结婚,好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充当壮劳力。
父亲说,相亲时,看到对方是个长着“猪肚子脸”的女孩子,他一点都不喜欢,因此断然拒绝,再后来还是克服万难去县城求学,并在那里遇到我母亲。
父亲每次说到“猪肚子脸”时,都带着一丝丝的鄙夷;而我总是想:好险!还好爸爸没跟那个“猪肚子脸”成家,不然岂不永远“沦陷”在农村?而且这个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我了。所以自此不管哪个女孩子、女明星再漂亮,但只要她的脸型是“猪肚子脸”,一定遭到我的“唾弃”。
不过我始终没有搞懂:在家里压根就不支持父亲上学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小少年,怎样就能“自动”的这么励志呢?
听母亲说,父亲到了县城后,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十八岁才上“高小”(小学四年级)。但他非常勤奋,也很有才,吹拉弹唱,打球游泳样样来得,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很漂亮。他的作文,曾在全县被当作范文,母亲也学习过,父亲因此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呢!
三

父亲学生时代的标准照。我小时候心目中的美男子,就应该是这样子。(作者提供)
父亲二十七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考上了四川西南政法大学,成了朝中乡第一个大学生,当时乡里曾轰动一时。
我印象中,父亲只给我讲过一件他大学时代的事,那就是打饭的技巧。
父亲说,大学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国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大学食堂开饭时,是八个人一桌,每一桌给一盆饭,大家自己盛到碗里吃。
那时每个人都饿得如狼似虎,饭一上来,大家都拼命盛上满满一碗,飞快的吃。父亲则相反,每次只盛半碗,然后也飞快的吃。因为他的饭少,所以总能先吃完,吃完后再狠狠的盛上一大碗慢慢享用。这样,别人吃到一碗饭,他却能吃到一碗半。
父亲讲这个故事时,脸上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还有一种农民式的狡黠。
不过,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次成功的利用这个方法抢到一碗半饭吃,因为母亲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曾被饿成“水肿病”,躺在医院里差点没死过去。
母亲还说,父亲这个大学上的很不容易,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生活费给他,他一到周末就得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卖苦力,当装卸工,扛很重的货物上下船,挣一点点零用钱来维持最基本开支。
1964年,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绵阳财贸干部学校做教师。那时母亲已在中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做了好几年教师了。
四
母亲的养父母虽是“无产阶级”,但她的生母后来改嫁给一个被共产党打成“恶霸”的人,母亲因此受到牵连,也成了异类,初中毕业后就不让她升高中了,当然就更不能再上大学。心高气傲的母亲觉得没脸见人,一气之下跑到远远的山里躲起来,当起了乡村教师。那年她才十六岁。
1965年,父亲与母亲结了婚,但却未能调到一起,彼此相距约两百里地。
1966年,他们有了我这个长女。也就是在那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我刚一岁,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当时他因急性肝炎正在住院,但也从医院拖到台上挨斗,双手被涂成黑色,以示他的“黑爪牙”身份。
挨完了斗,他还被责令抄写若干份检讨书,张贴到指定地点。
父亲身体虚弱到根本不能动弹,这项任务,只能由当时仍在绵阳休产假的母亲代为完成。母亲用布带将我绑在背上,一手拎着一桶用面粉熬制的浆糊,一手拿着一大卷用毛笔抄写的“大字报”检讨书,整整贴了一夜,才算完成“任务”。

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父亲挨斗,母亲将我绑在背上,连夜去替父亲张贴“认罪书”。(作者提供)
大约在我两三岁时吧,父亲被发配到偏远的四川省绵竹县汉旺镇。这是一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距母亲教书的地方大约也是两百多里。父亲“落户改造”的粮机厂建在荒凉的河滩上,几乎什么都还没有。
五

母亲抱着两岁多的我,与好友的合影。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免享受很多“特殊待遇”,比如拥有一个洋娃娃。两个妹妹出生后,家里就不再有钱给她们买洋娃娃了。(作者提供)
我四岁多时,大妹妹出生了。母亲无力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因此我被送到父亲那儿,开始跟着父亲在荒凉的河滩上过活。
父亲每年会带着我去探望母亲和妹妹一次。两百多里地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近,可在那时却觉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妈妈的学校在很深的山里。艰难的倒几次慢得像牛一样的长途汽车后,还要步行翻过好多个山头,走好远的山路,才能到达妈妈那里。
听妈妈说,第一次看着由爸爸带回去的我,她差点哭出来。我原来圆圆的脸瘦成了一小条,脸上似乎只剩下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最让母亲不能容忍的是,父亲给我洗脸时,只知道洗脸蛋上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他地方不管,所以我的耳朵背后一直到脖子上,都积着厚厚的污垢。我的两个小羊角辫也被爸爸扎得一高一低的,根本不对称。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儿变成这样,妈妈很伤心。
有一年,我和父亲要从妈妈那儿离开前,妈妈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到家后再给爸爸。
我第一次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兴奋得不得了,不知道拿那封信怎样才好,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刚走完山路,还没坐上长途汽车就交给了爸爸。爸爸看完信,二话不说,背着就我往回走,回到妈妈那儿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倒在床上。我吓坏了,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特别害怕妈妈责怪我没听她的话,提前把信交给爸爸。
多年后,我才隐隐了解到,当时妈妈在信上提出要与父亲离婚——这样分居两地的艰难日子,她实在是过够了!
据说爸爸当时曾“以死抗争”,才勉强打消妈妈的离婚念头。母亲年轻时是中江县城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父亲上大学时不停的给母亲写情书、情诗,每封信都变换不同的字体。父亲的字很漂亮,诗也写的格外动人。他的才气和恒心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大才子会在一夜间变成“黑爪牙”,“黑爪牙”家属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
六
一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才被允许与爸爸团聚。这时我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终于在建于河滩上的小平房中过上了“团圆”的生活。
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其匮乏的年代。父亲是他所在工厂唯一的大学生,母亲在汉旺镇小学当老师,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黑五类”家庭,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怎么也是个“异类”。母亲甚至不鼓励我与其他孩子玩耍,怕万一小孩子间有了争执打起来,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而把父母也牵扯进去,让一家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许多个盛夏的夜晚,别的孩子都在外面乘凉、嬉戏,我却独自呆在家里。河滩野地上蚊子特别多,我只能把自己关在闷热的蚊帐里看书,汗水嘀嗒嘀嗒的掉在书上。
看书是我孩童时代唯一的乐趣。可是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太少,很多名著都被当作“毒草”烧掉了。
为满足我的阅读欲,父亲开始写儿童故事给我看,慢慢的也写一些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父亲本来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嘛。
父亲的故事都是写在横格稿纸上,用棉线装订的整整齐齐,是名副其实的“线装书”,而且是绝对的“孤本”。
很多时候,我是父亲作品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读者。母亲一旦发现父亲写的东西,哪怕是给我写的很“革命”、很迎合“时代潮流”的“红小兵抓特务”之类的故事,她也一定将之付之一炬。
每次母亲烧父亲的线装“孤本”时,父亲都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让我感到非常不祥、非常害怕。
那时,唯一快乐的时候是过年。爸爸的毛笔字很漂亮,工厂所有的大标语都是他写的,很多人也会来找他写对联。每到过年,他也一定给我们自家门上贴上春联。他的手很巧,除了会缝衣服外,还会做木匠活儿、会打家具。家里很多桌椅板凳等小件家具,都是他亲手做、亲手刷漆的。过年时给我和妹妹们做个红灯笼、兔子灯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
我和妹妹拉着爸爸给我们做的有四个木头小辘轳、可以行走的精巧的兔子灯在街上“招摇过市”时,总会引来羡慕的眼光。要知道,那么漂亮的兔子灯,小朋友们见都没见过,更别提去哪里买一个了。那时我们好开心啊。
七
小学四年级时, 突然听同学讲:“江青是个大坏蛋!”
我被这“大逆不道”的话吓坏了。江青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吗?怎么能是大坏蛋呢?这个同学敢说这话,不得是个“现行反革命”?
但没过多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真的被打倒了。我那时并不知道这就意味着给无数人带来无穷灾难、让七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只记得我所在的学校文艺表演队,被要求站在大太阳下,在马路边列队迎接将从县城运来的《毛选五卷》。
那天太阳好毒啊,晒得马路上的柏油都化了,所以当《毛选》终于由长长的车队驮运着抵达,我们被要求载歌载舞跳起来时,我的鞋子却被熔化的柏油粘的拨不出来,急得我直想哭。
八
又过了一阵,突然听说要重建“文革”时期被砸烂的“公、检、法”,很需要专业人才,要调爸爸这个政法大学毕业生回绵阳,到新成立的司法局工作!
绵阳!这是仅次于省城成都的地区级首府,是一个屡屡听说、记事后却没再去过的地方,我不禁很有些神往。
不过,“组织上”没有安排妈妈同爸爸一起去,原因是没有妈妈的“编制”。
虽然再次分居绝不是父母想要的,但,能从被发配的边远小镇回到大城市,并做专业对口的工作,总是符合“人往高处走”的古训。再说,父母认为我和妹妹若能到绵阳去上学,以后能考上好大学的概率更大。不然,总窝在只有一条小街的小小的汉旺镇能有什么出息?拿妈妈的话说,汉旺镇的这条小街短到“一个跟头就能从街头摔到街尾”。我那时学习成绩在汉旺镇小学虽然年年第一,但妈妈总不忘提醒我:“这是矮子里面充将军”,让我记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这样,为了两代人的前途,在刚刚过了几年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后,我们的家,再次被拆为两个,我和大妹妹跟随父亲来到绵阳,小妹妹跟妈妈则留在汉旺镇。

为了两代人的前途,我们的家再次被拆为两个,我和大妹妹跟随父亲来到绵阳。这是刚到绵阳时的合影。(作者提供)
九
绵阳市司法局是新建的,既无办公楼,亦无职工楼,只在招待所里租了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父亲住男生宿舍,妹妹住爸爸单位的女职工宿舍,我则成了“住校生”,住在我就读的绵阳南山中学学生宿舍,三个人住三个不同的地方。南山中学在半山腰上,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味道,据说清朝时曾是科举考场。周末我下山回“家”时,就与妹妹挤在同一张单人床上,同一房间里还有好些爸爸单位的女同事。
偶尔,爸爸会用电炉在办公室煮点东西给我和妹妹吃,算是打打“牙祭”,让平日只能在食堂“抢饭”的我和妹妹解解馋。
就这样,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三年多了,妈妈也未能调到绵阳来。一家人只能坐着长途汽车在假期时跑来跑去互相探望。妈妈常说:“好容易挣点儿钱,都压了车轱辘了!”
十
不过,爸爸的工作好像慢慢有了起色。先是听说司法局下又新设律师事务所了,他调到那里当律师了,后来又听说他居然被评为“四川省十大律师”之一了!
听人说,爸爸最风光的一次,是一人舌战对方的三名律师。对方是个全国特级教师,在当地很有名,也有能力一口气请三名大律师来替自己的辩护。但三名大律师都败在了父亲脚下,输了那场官司。
听到这些,我一方面很骄傲、很神往、很想到法庭上去看看父亲“舌战群雄”的英姿,另一方面又有些难以相信,在我印象中一直木讷少语,在家几乎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的父亲,怎么就能成为需要出众的口才方能胜任的大律师呢?
有一次我偷偷问他:听说你当律师以来从未输过官司,秘诀何在?
他诡秘地一笑,说:“我从不接会输的案子。”
这时候,父亲脸上浮现的笑容,仍然是既有孩子般的天真,又有农民式的狡黠,让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个什么“十大律师”。
十一
我读完高二、将上高三时,需要在学文还是学理之间做出选择。当时我文理科成绩差不多,许多人都说,由于大脑结构的差异,女孩子最好是学文科,学理科最终会输给男生。我自己除了想上北大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外,对到底该学文还是学理很是举棋不定。
父亲坚决地说:“学理科。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
父亲说完“1+1永远等于2”后,再一次铁青着脸,以他特有的方式咬着下嘴唇,跟我小时候妈妈烧他写的书时的表情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不祥和害怕。我什么也没敢说,乖乖的就选了理科。
十二
1984年,我如愿考上北大,学的当然是理科,地球化学专业。要离开已读了三年的南山中学时,因为一直住校,所以有不少行李。父亲蹬着三轮车到学校替我搬行李。沿着盘山路往半山腰上蹬车很费劲,汗水很快就将父亲的衣服湿透了。
父亲一边流着汗,一边笑着说:“我是个快乐的三轮车夫!”他的笑容中还有一丝讨好的成分。
父亲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知识分子,生活中几乎从不表达或流露自己的感情,也从不曾对三个女儿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肉麻”话,但那一刻父亲一边流着汗一边说自己是个快乐的三轮车夫时的讨好表情,却永远温暖的驻留在我心中。
对于我,那便是父亲的慈爱。
十三
大学二年级时,我接到父亲来信。他告诉我他入党了,语气很正式,似乎还透着一丝丝的激动。
这多少让我有些惊讶,甚至很是惊讶。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来不会在家中谈论政治或国家大事,更不会跟女儿们讨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选择专业时,父亲那句“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的“名言”,应该是我从小到大听到的父亲唯一一次带有一点政治色彩的表述。
父亲到底为什么入党?是对这个党仍然充满希望,还是入了党后不会再被视为异类而受到排挤?

我上大学时,父亲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学校看我。这张摄于北大未名湖畔。(作者提供)
十四
大学三年级时,在政治辅导员的动员下,我也上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回想起来,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父亲的入党。从小母亲就常说父亲偏心,在三个女儿中最疼我。反过来,父亲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我很在乎父亲所做的选择,和父亲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想,他在遭受那么多坎坷后,仍然愿意入党,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党还有希望。
另一个原因,是我听信了一种说法: 虽然党还不够好,但更多如我一般的好成员加入的话,难道不可以从内部改造、改善它吗?
其实细究起来应该还有第三个原因。从小到大一直是“三好学生”的我,生长在一切社会资源都被中共控制的社会,从小就认为,“学习好”、“表现好”是应该的,入队、入团、入党,是一个好学生、好社会成员自然而又必然的人生轨迹。
就这样,我成了全班第一名党员。到大学毕业时,我们班一共也只有两人入党。
十五
再以后,我毕业、工作、结婚、生女,一切都在符合父母预设的轨道上进行着,不但上了名校、拿到硕士学位,成功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多少人打破头也挤不进去的好单位,同时也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时父母跟谁说起我来都笑的合不拢嘴。我考上北大那年,大照片还被挂在绵阳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大门口,作为绵阳“建国三十五周年教育成果展”的一部分展出。据说这个“成果展”,特别是其中我的大照片,在每天都万头攒动的人民公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许是因为人们觉得,南山中学有人考上北大不算太稀奇,但一个看起来明明就是“绣花枕头(一包草)”的女孩子考上北大,就比较少见了。
我那时已离开绵阳去北京上学了,本来并不知道这个“盛况”,但一时间,我接到数封陌生人从绵阳寄到北大的信,有表示仰慕的,有讨教学习经验的,让我莫名其妙。向家人打听,才了解到“原来如此”。(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