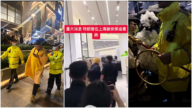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讯】在安仁民间方圆几十里,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
《收租院》的故事是四川当局的一些人当年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
由于害怕民众揭露他们的谎言,尤其是居住在刘文彩庄园周边民安村的民众。他们知道的真相最多,而且最容易接近来庄园接受“教肓”的参观者,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编造刘文彩谎言最早的受害者。
1960年春,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那里。
民安一队的贫农刘直君夫妇去后不久就双双饿死在八管区。死时两个儿子还小,由他人领养,一个去了温江养鱼塘,一个去了崇州中和场。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也在去后不久饿死在八管区。8岁的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
民安一队的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国元,是乡镇文书,发配到八管区后看到很多人饿死,便写信向上级反映,其中有“娃儿饿得尽叫喊,大人饿得倒偏偏”两句。上级就以反革命罪把他逮捕判刑,并五花大绑地押到农村各地批斗,不到半年就死在牢里。死时年仅31岁。刘国元的母亲看到儿子受难,肝肠寸断,活活气死。29岁的妻子杨开玉拖着不到十岁的五个孩子和一个老母,其艰难无法言说。老家的亲人去帮他干农活时,看见五个饥饿的娃娃围着杨开玉要吃饭。由于贫困,更由于是反革命家属,三个大孩子都无法读书。杨开玉守寡至今。
民安一队的刘体忠,是个起义人员,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此次发配到八管区的人家至少有十余户,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至少还有刘用箴和刘福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
1964年,本地民众多次向来庄园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当局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1964年的发配是拿民安一队的刘富田来作开刀人。
刘富田过去曾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后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分时定为贫农。1964年9月初前后,当局以刘文辉的伪军官为名把刘富田抓起来,凭空诬陷刘富田是反革命,还诬陷他偷牛,他们指使民兵队长郑泽安把他反吊起来毒打逼他承认,又威胁他的亲弟弟刘富成来作假证,来“揭发”他。刘富成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恐怖政治的威胁下被迫作假证说他哥哥偷牛。当局利用刘富成屈从威胁是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逼他说刘文彩强迫他搬家,这些都是后话。本地人都说刘富成乱说,都鄙视这家人,而刘富成也给大家表白过,是上面逼他乱说的。
在日复一日的酷刑下,熬不住的刘富田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整刘富田是为了制造恐怖,威吓民众不敢“乱说乱动”。果然,民众吓住了。
1964年10月1日安仁开大会,刘富田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工作必须当天完成。逮捕刘福田已经把人们吓住了,接下来的驱逐令更是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没有犯过任何法,没做错过任何事,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凭什么驱逐我们?当局根本不考虑无辜者的死活,他们就是要制造冤案,就是要制造死亡和苦难,使民众感到恐怖不敢出来揭露他们的欺骗宣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极度的恐怖中,这些被驱逐者只好离开自己的家。
这些人被发配到外乡,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所有被驱逐者都被定为“坏人”,在新地方他们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在极左年代,只见把受迫害者押解回原藉劳动改造,从没见过把无辜者从原藉发配他乡。刘福田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其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别人讨个生路。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床都没有,哀求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9月25曰,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当年28岁的刘世炳也被驱逐。他毕业于新津师范校,原是教师,其妻廖秀芳是共青团员。刘世炳认为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分的,自己又没犯过任何法规,凭什么没收自己的房子和家具。他找当局评理,根本没有用。回来时房门已上了封条。刘世炳见状气愤已极,上前把封条扯了,夫妻双双进门回到家中。当局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当天晚上刘世炳有很大危险,好在有人把险情告诉了他,他吓得立刻跑到外县去了。晚上民兵来的时候,家里只有共青团员廖秀芳,她还背着自己不到四个月的儿子。民兵进门就上前把她绑起来押往发配地,押解途中路过徐大石桥时,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好在被人拖了回来。
被驱逐者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寡妇廖素瑶,因她三十几岁才嫁人,所以在扫地出门时两个女儿才分别15岁和17岁。这家人本来就过得十分艰难,当局也不放过她们。在发配途中小女刘世伦扑到水里,到了发配地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没有哪来钱治病?一个月后的一天,廖素瑶饿得昏倒在地,两个女儿哭着喊妈妈,她们把仅有的一碗稀饭喂了妈妈,廖素瑶醒过来了,小女刘世伦倒下死了。死后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边的墓地来安埋,当局害怕这幕惨剧激起民愤,于是说廖素谣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共产党示威,立即派民兵把廖素瑶抓来批斗。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他俩有个未满三岁的儿子贵伟,被扫地出门时孩子受到惊吓,发配地的凄凉孩子无法接受,于是小贵伟成天哭喊着“我要回去”哭了整整一个多月,活活哭死了。儿子死后不久,刘世英也因劳累过度成了残废。
在此次从原籍发配他乡的过程中,主管部门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了,在恐怖下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如陈建中和刘世伟等。
在全国铺天盖地宣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故事,从1958年10月组建专业班子到1964年10月第二次大规模发配本地民众,已过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六年中编的刘文彩故事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下流。1964年10月,当局又肆无忌惮地进入编造刘文彩《收租院》的阶段。
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艺术家们又说刘文彩每天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你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生活,你应出来控诉他。谷能山回答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急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接着给他作了许多工作,后来又对谷能山说:你是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是好人;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你要给他划清界线。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
谷能山的儿子对刘小飞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告诉刘小飞:他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他有个儿子在那里)。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有什么两样?
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
《收租院》里有一个因为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的故事。罗二娘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奸她。罗二娘第一次诉苦是在安仁的星廷戏院,当她说到上面那些事时,加之她使用的语言很污秽粗俗,本地听众当场吐口水,口里发出鄙视的啧啧声,还有的人说:“你(罗二娘)洗干净没有?”,就是安仁公社的妇女主任汪桂清(共产党员)都说罗二娘“稀鸡巴脏的,刘文彩把她看起了!”
安仁的许多民众告诉刘小飞,当罗二娘诉完苦走到街上,她的长子罗学成当众说她:你不要脸,你去乱说别个(指刘文彩),过去我们的锅烧坏了还是别个送给我们一口锅,别个看我们穷还送一头猪给我们喂。罗二娘的亲侄子,现年82岁的罗大文告诉刘小飞: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
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清”运动时大邑县朱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朱部长为此还给了罗二娘一座公馆。罗大文还说罗二娘死后脸给耗子咬了两个洞,乱说耗子就要咬。罗大文还说过去每到过年,他们家和二娘家都得到过刘文彩发的钱粮。
本地民众还告诉刘小飞:罗二娘是本地长相最丑最不爱卫生的婆娘,本地没一个人答理她。正因为受人冷落,有一种发泄欲,罗二娘才为当局利用。罗大文和好些民众告诉刘小飞:1960年前后,罗二娘的丈夫罗吉安饿死,罗二娘的小女儿饿死,罗二娘的大孙子饿死,罗二娘的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四口人。刘文彩从来没伤害过罗二娘,罗二娘怎么来诉刘文彩的苦呢?
更可笑的是,现在还把罗二娘的故事放在《收租院》里,《四川日报》副刊负责人王治安在他的大作《轰天绝唱收租院》里还把罗二娘的故事作为他的重要举证。
《收租院》里最有名的是水牢故事,说刘文彩把交不出租谷的冷月英抓来关水牢。现在官方己承认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了。而当时却强迫各阶层的人士来作假证,以图弄假成真。据现居安仁附近虹桥村12组的龙玉庭(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今年86岁)讲,当年政府把他叫到庄园去让他说地下室是水牢,他(龙玉庭)说不是,政府的干部就说他:你晓得个球!又说他(龙玉庭):你现在还在说他(刘文彩)好!龙玉庭还说住在一把伞的李蒙松因为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就被抓去劳改。庄园档案里还记载了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亲自出马逼民主人士王安懋,刘树成作假证的材料。
虽然当局现在已承认“水牢”故事是虚构的,是假的,但李蒙松和许多冤案受害者却没有平反,这是为什么?
《收租院》里还指控刘文彩把交不够租的人卖去当壮丁。当地人却说刘文彩保境安民,谁家的人被拉了壮丁,只要告诉刘文彩,他就一定去给你讨要回来。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逼租,根本就没这种事。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16组18号的唐学成(今年77岁,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讲了一件事: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第四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你回去吧,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回答“是头黄牛”,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们。
唐学成还说他们队的李配云和兰田大队14队的母德鲜都得过刘文彩送的牛。唐学成还说他们队的李洪顺家很穷,刘文彩就买了一头小水牛送给他们。送唐学成的那头黄牛解放后被入了合作社,从此不再属于他们。
《收租院》里说交租的人充满对刘文彩的阶级仇恨,现在还在的民安三队的老佃户李福清(90岁)对刘小飞说:去了(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还证实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子也带去吃饭,后来《收租院》就编造小孩子也去给刘文彩交租。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央视副台长陈汉源当年拍的电影《收租院》里有一段解说词:“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穷人的仇!”这段文字还编入小学的教科书。可是,刘文彩的乡亲从不认可这段文字,刘丙南、陈育维等老贫农说这是乱球鸡巴说的,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说这是吃屎(知识)份子编的。
陈汉源拍的电影《收租院》里出现了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冷月英,一个是陈孟君,这两个人与刘文彩都没有任何关系,全是假的,全是假证。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的铁板租把农民一年的收成剥削得干干净净,事实不是这样。
采访片《大地主刘文彩》中有采访者问本地老人:刘文彩收的租多不多?老人回答:“不多”。情况是怎样的呢?
四川是天府之国,一年收两季,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谷子,平均一亩一石,也就是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而众多的老贫农,老佃户都说后来在毛时代交的公粮比给刘文彩交的租多许多。
安仁的一个生产队长罗友志讲那时上公粮上米每亩350斤,上麦子200斤。刘文彩只收一石谷子,折合米只有290斤。
在此我讲一件采访到的事情:从四清运动开始,每个生产小队就安排一个工作组的人来与农民同吃同住,监视农民,每天不停的给农民洗脑,搞大批判,批判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在那恐布的岁月依然有人公开说真活。
如安仁合兴二队的罗建庭(女儿罗淑英现住一小区广场附近),当时他说:过去没吃的时候去找刘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来了,现在去找公社,这个批那个批,人饿死了都没批下来。他说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于是大家就帮着传这句话,传得非常广,非常远,后来传到当局那里,就派民兵去把罗建庭抓起来开大会批斗,会完后当局威胁群众,谁再讲这种话抓住了后果自负。
《收租院》塑有一个交租的小女孩,说她“她小小年纪,就已经感到这个世道的罪恶与不平!”这个小女孩就是上面提到的老贫农李福清的女儿李金容。李福清一家都说《收租院》的那些事是瞎编的。
《收租院》的解说词的笫一部分是:送租;第二部分是:交租;第三部分是:算账;第四部分是:逼租;第五部分是: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刘小飞把这些文字读给本地的老佃户,老贫农听,他们都说是瞎球编的,李福清说是吃屎(知识)份子编的。
90岁的李福清还说:刘文彩在的时候,这一带没有饿死人的事。民安三队的老佃户罗辉武说:那个时侯那有饿死人的啊。
刘文彩故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的马识途,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不慎透露了人民公社时期四川农民交公粮的情况:“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见《龙门阵》1995年第三期第7页) 这些场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实写照嘛!怎么拿来栽在刘大善人的头上呢? 文章还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说省档案馆记录的是810万人。这不真实,据老干部邓自力(邓小平的兄弟)的回忆文章《坎坷人生》中有这样的记载:“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摘自《坎坷人生》265页)
那些年大邑县又饿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县县志上有历年的人口统计,
现摘要列出: 公元 1950年303350人
1958年346770人
1959年317673人
1960年295188人
1961年281491人
1962年280906人
由此表可看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而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是在那几年大饥荒年代中着手编造的。也正是那个民众大量饿死的历史背景,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才拿来疯狂炒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收租院》故事里还有几个不是刘家的人,其中一个是李育滋用绳索勒死穷人李国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天大的冤案。当年李育滋把李维嘉、周鼎文等一大帮共产党员保护起来救了他们的命。解放后这些人恩将仇报,反咬他是大地主大恶霸镇压共产党,把他抓起来施以酷刑,先是吊打,手臂吊断后又把他的左眼球活活挖出来,在枪杀他的现场,周鼎文还高高坐在审判台上。李育滋死后,他的心脏肝脏和生殖器都被挖了。李育滋一家八口人死来只剩下三口。李维嘉、周鼎文这些党员,又把他们制造的冤案放到《收租院》里,作为地主阶级的罪恶来展出。
《收租院》里还有一个恶霸地主陈玉堂的故事。当年陈玉堂把他的家长期提供给李维嘉,周鼎文等共党员作活动据点,无赏给他们提供食宿,掩护他们,还把自己仅有的30多亩好田全部送给这帮共产党。土改时周鼎文等人恩将仇报说他是恶霸地主,把他抓来受尽酷刑和侮辱后枪杀了。
刘小飞在调查中得知陈玉堂全家已死光了。这些人都成了马识途,李维嘉集团编造伪历史,骗取政治本钱而杀人灭口,杀良冒功的牺牲品。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过去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伪钞,杀人抢人时使用的两块造假币的石印版,也放进刘文彩庄园作为刘文彩的罪行展出,说“刘文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还私印伪钞,铸造假币,榨取劳动人民血汗”。
《收租院》里曾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以阶斗争为纲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有段是这样写的: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收租院’的悲剧重演,万恶的地主庄园再现,他的黄梁迷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被革命人民击得粉碎。历史岂容逆转,复辟不得人心。今天我们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高歌猛进。”(《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调整充实展出内容文字说明》)
《收租院》里还有许许多多荒唐的故事,全是捏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局把《收租院》的故事编进中小学的教科书,又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反复放映,更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炒作,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汉马功劳的刘氏家族成了宣传的牺牲品。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被官方从原籍发配他乡,他被迫远逃他乡,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他为人友善,从不与他人结怨。
由于《收租院》的宣传,说刘文彩迫害农民,那里农民便把刘世伟全家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是用绳索勒死的。
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成都铁路局弄去劳动改造,也死在外面。
主管当局疯狂迫害刘文辉家族,刘文辉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干也不能幸免。1965年四川当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干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听说还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的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那里根本不予理睬(可见是故意的),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干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刘文辉的长女婿,主要起义将领伍培英在1966年被逼自杀。
主要起义将领刘元瑄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抗日将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因自习英语,主管当局的人(有人说是安师吕)怕他向外国来宾用外语揭露刘文彩的真相,借口都不用就把他抓去高山劳教所关押,邓小平上台后才放出来,那时刘世海已被逼疯了。一天夜里一架城管的车把他拉走,从此他从安仁民众的眼中消失,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几年前生产队把刘世海的宅基地拍卖了,看来他已经死了。
《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述,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曹克明死前,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编造《收租院》故事的那些人,可以随意制造冤案,随便抓人,而执法机关处于仆从地位去配合他们。《收租院》就是这样编出来的。这样的《收租院》能称之为艺术品吗?!
编造《收租院》的那个班子,在1965年10月完成《收租院》的编造后,又乘胜挺进创作出了泥塑《农奴颂》,这是反映西藏上层与达赖的奴隶制的群塑,规模内容与《收租院》大同小异。《农奴颂》完成后,当局准备把它到刘文辉公馆里展出,后来高层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未同,主管当局才作罢。
当年《收租院》进京,据说盛况空前,但周恩来却不去看这个把戏。现在主管当局还在大肆吹捧《收租院》的什么艺术性,思想性。当年中宣部的周杨说《收租院》是“中共建政以来两大雕塑之首(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998年刘小飞从大邑县城乘中巴车去安仁的路上,当司机得知他是刘文彩的孙子时,他对刘小飞说:“我爷爷今年95岁了,现在还在,他说的,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B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有了当年老佃户的这句话,《收租院》所有的艺术艺和它所有的思想性通通落得分文不值!
在此恳请各界人士和相关部门派专人来调查刘文彩事件的真相,不要再让那些冤案的制造者在台上掌控话语去年主管当局把《收租院》运到法兰克去展出,我真不明白他们在宣扬什么。据说德国的卡塞尔大学还专门研究《收租院》,我请热心的朋友把这篇文章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真相,不要被骗了。十年前有意大利的一个什么机构还授予《收租院》金质奖章,他们知不知道事件真相?!在此希望热心的朋友把这篇文章传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相,收回奖章。
在此我恳请各界人士和相关部门派专人来调查刘文彩事件的真相,不要再让那些冤案的制造者在台上掌控话语权,装模做样地欺上压下,还受害者的荣誉!还受害者的公道!
最后,因本人不会电脑,无法上网,故请求朋友帮我转发,愿这篇文章像《收租院》的宣传一样,传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