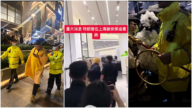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9月17日讯】引言:语言的政治学
教育从语文开始。在多种意义上,语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础。首先,学习语文,特别是语言,是教育的起步。这从幼儿呀呀学语就开始了,起步远远早于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语文是进行其它教育(特别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语言为基本载体。再次,语言是人们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本身就成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后,语文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基本工具,还构成普遍意义上的长期(或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总之,可以说,没有语文,就没有教育;语文教育是最为基本的教育。
然而,与其它很多方面(如数学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和社会性,并不构成它对政治的免疫,反而为政治的介入敞开了大门。在一个具有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遗产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历史上都高度重视语言文字的社会,也尤其如此。事实上,语言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关系。它一方面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过来给予政治变迁以重要影响。所以,“语文的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而非语言学的角度),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初步的探讨。
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文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于民主化的前景,观察和分析目前中国的语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层面对民主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托克维尔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为深刻的观察家之一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在美国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过,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还鲜有这一方面的文献;而在中文语境中,这更似乎仅仅是一种尝试与开端。本文因此很难对此作系统的论述,而宁愿从一种具有语言社会学含义的普遍而突出的现象即中国语文的“二元化”现象出发,借助政治科学的一些概念,联系政治制度转型,初步地探讨这一语文教育所生成的社会语言现象如何帮助维持政治专制,以及其对于中国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义涵。
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裂:中国语言的二元化现象
什么是所谓“语言的二元化”?请允许我从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说起。
在某种程度上,听中国话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后的香港,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讲普通话。本来,对我这样一个大陆背景、完全不懂广东话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语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说,还因此少受当地人的歧视。但是,颇有一些人,是从电视或与官方人员的交流中学习普通话,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分子”们。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学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学院来的一个访问团,本校一位专责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层官员,在饭桌上一口一个”共和国”如何如何。还有,回归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辈子受英国教育的高级官员们,已经学会了拉着长腔讲话,并随时停顿以接受听众的鼓掌。这些作为,从词汇到腔调,由于那种学习过程中所特有的夸张,恰恰凸现了中国语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种途径是电视。最近几年,香港的收费有线电视中外国频道越来越少,中国频道越来越多。比如说,我所在的学校教授宿舍区的有线电视,一共大约十个频道,除了三、四个香港本地频道之外,原来大约有一到两个普通话频道(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是凤凰卫视),另外的多是各国电视,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今年以来,后者则减少到只剩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商业电视频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资电视频道(仅中央电视台现在就占三个频道,包括普通话和英语广播;事实上可以认为是中央电视台海外分部的凤凰卫视又占了三个)。打开电视,常常听到的就是那种拿腔拿调的广播。本文写作时,正是“六一”前后,电视上多是有关儿童活动的报导。听到那些孩子们也假模假式地说话,只能愈发感受到在中国语文教育被政治践踏的病态。
我这里还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说假话。我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存在一种“假语言”。通过语文教育,中国语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语言特点,就是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两个基本元素即词汇和腔调上的二元化。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像电视播报或像官员讲话那样说话;而电视播报和官员讲话,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这些播报者和官员本人的说话。如果以日常生活语言为“真”语言,则另一种语言即“假”。“假语言”与“真语言”形成两个世界。前述本校官员尤其可笑,就在于他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区别,把电视上的话搬到饭桌上来讲。
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与其它社会,比如说,美国,做一个比较,中国语言的这种“二元化”就更是显而易见了。美国总统在官式场合讲话,当然严肃郑重的多;但是,他的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有多大区别呢?那么多的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在电视上讲话的语速、腔调等等,与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说话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区别不大,则我们即更加疑惑:为什么中国语言就有这样一个“二元化”的特点?这一特点,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场合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与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质有什么关联吗?它又会反过来如何影响公共生活呢?
“假语言”、“真语言”与人格分裂:语文教育如何维持政治专制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国语言的这一“二元化”特质,是长期政治专制制度的产物。
在民主政治下,为了取得选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言说话;因此,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本来也会随时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正像托克维尔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观察到的一样,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它事情确定规则一样。
中国政治的吊诡,在于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却又标榜“人民民主”,也确实是二十世纪人民革命的产物,并从来都趋向于某种民众主义(populism)。表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会,具有贵族语言与平民语言的“二元化”,也当然不像民主社会,语言趋于一致;而是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观察到的公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二元化”。前者并不完全属于官员,后者也并不完全属于民众。无论官员或民众,只要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当然官员更多地拥有这种机会),就会官腔官调;而即使是官员,日常说话也会回归后者。
这样一来,所谓“公共语言’实际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础--这是我们称之为“假语言”的根本原因。传统权威主义社会的贵族语言,仍然具有其贵族生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它可能主导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但这种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实的,包括真实的不公平和真实的权威主义。中国今天的情况与此不同:所谓“公共语言”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语言,就像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虚假的一样。其直接政治影响,就是人们习惯于用“官腔”来对待公共生活(也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中形成两面人格。这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人们使用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就当然地尊重那种语言所蕴含与表达的价值观念,遵循那样一种游戏规则;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则回归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尊重另外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这样,人们就普遍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现象。
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两套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明显地处于相互抵捂甚至冲突的状态。身处其中的人们,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呢?看来,他们的基本战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与所谓公共生活完全区隔开来。这就像演员演戏,明明知道戏剧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上了戏台,就要用那种语言那种腔调讲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演戏与现实的最大甚至是唯一关联,可能就是演员要借此为生。同样,在目前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套所谓“公共语言’有什么真实意义,但是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讽刺在于:那个虚假的语言世界,就政治层面而言,却同时也是一个真实世界,甚至是一个比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更为坚硬因而更为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专制政治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构造与存在。它有其虚假的一面,那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承认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实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权力使用。由于人们可以退回日常生活,于是大家就假装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装”确实不过是“假装”。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他们为此愿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种“假装”;但恰恰是这种“假装”,一则麻痹了人们的良知,二则模糊了人们的认知,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无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专制状态。对专制政权和一般民众来说,这种“语言的二元化”都成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专制政权容忍真实语言,因为一般民众因此愿意与“官方语言”妥协;一般民众需要“官方语言”,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专制下生存的起码技巧。通过包括学校、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语文教育,这种语言二元话与人格分裂成为正常状态,政治专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还原真身份:真实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政治专制的民主化转型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化时,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种看来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那些昨天还在那个制度下“假装”的人们,为什么在那个晚上突然决定不再继续“假装”下去,而要完全抛弃那个制度?在有关这场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那里的人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私人愿望(private preferences)与公共愿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状态;他们虽然私下早就对这个制度极度不满,但是不敢确定别人也是这样不满;他们甚至能够蒙骗自己,认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政府和这样一种制度。而一旦当某个机遇使大家相互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意愿时,革命就在一夜之间完成了。
中国其实早就走出了这一阶段;现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确定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对于这个制度非常不满。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间,人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了这种不满的积聚程度。问题是,在这之后,出于恐惧,人们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当局则在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隔,给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间你则容忍政府为所欲为。但是,人们是不可能仅仅生活在私人空间的,他们必定同时生活在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于是,我们看到,89之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人们小心谨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间冒犯当局的局面;人们在这里继续使用当局的语言说话,从而“假装”出一副相信当局并愿意与当局合作的姿态。对这些“实际上”不再接受现政权和现制度的人来说,他们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过是在“假装”;可是,对于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仅仅这种“假装”本身,已经就是一种富有而强大的资源,可以支撑自己了。
这也等于说:一旦人们不再“假装”,中国政治的巨大转型就会发生。在公共空间以日常的真实语言说话,就是抛弃“假装”的第一步。这也就是让每一个人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成为他(她)自己,而不仅仅是在面对自己和亲朋的时候才成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真话”,那主要涉及的是内容的判断;我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真实的方式说话”,那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真实。打一个比方: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意见,可能你真的是在说谎,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别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从而建构起具有起码意义的真实”公共空间”。而从这样的公共空间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经提供了许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文章来源:《新世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