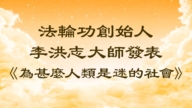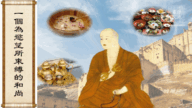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1月1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嬗变
第四节:十年生死两茫茫
1959年我被重庆大学强迫扣上右派帽子,无理踢出校门,送往南垌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留在我心坎上除一腔冤屈怨恨外,还有一个对我亲人的牵褂,该如何处理这骨肉分离之痛?
当时我很渺茫,看不清地狱前方何处才是尽头?想到抚养我的老人忍着从心头割肉之痛,我的心便像被刀割般难受。
外婆和弟弟在父亲被捕时,已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重创,接着又是母亲划为右派,这雪上加霜后,现在我又遭入狱大难,当时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们,给他们层层创伤的心上再洒上一把盐。
既是中共菜板上的肉,把我们一家赶尽杀绝,我们就只好忍受这“灭门”之灾的降临!
入狱后把一切可怕的后果埋藏在我的心底,万般无奈中,我只有选择不告而别。十九岁的我要像男子汉一样独立承担一切,但家人将承担怎样的挂欠和伤痛。
剩下的孤儿寡母会不会踏遍千里寻找天涯沦落的我?常使我陷在不知如何处理的两难之中!我只能如此了。
入狱开始的那段岁月里,我往往在夜半睡梦中哭醒。
最后,一个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信念控制了我,当时想,除非我从监狱里沉冤昭雪那一天,我能体体面面的回到亲人中去,绝不会以“带冤”之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主意打定,我就突然消失了。
从此就再没有向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任何关于我的信息。从那以后,我独自任由劳改队发沛冲军,从一个鬼门关到另一个鬼门关。
算起来,我在狱中渡过这段日子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透过瓦背上挤进来的月光想念他们。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会摆着从厨房端来的饭菜,默默地坐在我的铺位上,面前摆着四个碗和四双筷子,合著掌,祈求他们在远方平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千里孤飞的失群之鸟,终有回巢的时候,“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悲歌•乐府
对亲人长年的眷念,像一杯永远无法喝尽的苦水。屈指算来,我已“三十五岁了。先前还是一个稚气的孩子,十五年已变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如果那倚着竹篱,盼我归来的白发外婆还在人间,那么她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有一天,心灵的感应像一股强电流聋击着我,使我强烈地感到一种说不清的预兆,隐约感到这些我日夜萦思梦绕的人都不在人世,
一种不能再与他们相会的恐惧催促我,我不能再音信杳无的继续下去。否则,我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他们了,那么就算我从这里活着出去,我将要终身负罪,我既对不起日夜盼我归来的老外婆,也对不起艰辛中抚育我的母亲。
(一)寻母
1973年春节期间,就在这股寻亲思潮的冲击下,我结束了十五年的固执。第一次提笔向母亲写了狱中给她的信,全信仅用了一百多字,因为十五年的变迁,我不知现在我到那里去寻找他们!该怎么去寻找他们?
“妈妈,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仍按十五年前的地址试着写这封信,倘若你能收到它,就请立即回我的信。我这是在四川西南边陲上一个小县城里给你写信,希望这封信能接上我们之间已断了整整十五年的联系。
您的孩子孔令平1973年2月于西昌盐源909信箱六中队。
这一百字寄走了我整整十五年对亲人的朝思暮想,也寄走了十五年筑成的自闭,我想这封信她如果不能收到,那么至少告诉我一家人全都亡故,倘若这封信寄到她手里,那么我估计得出,在这个文字狱紧锁,我们间唯一可沟通的窗口上,魔鬼正用怎样的眼睛监视着这些信!这第一封信,必会受鬼蜮们的盘查,嗅出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然而这一百个字,堆积整整十五年的血泪意欲喷溅出来。就宛如一个丢失了母亲整整十五年弃儿的呼喊,在误入地狱的不归路上,寻找归途!寻找她的喊声!
所以我纵有再多的怨恨要倾诉,但委曲和苦都不能露出丝毫,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徒生枝节,不但我这一百多字不能打破关闭了十五年的亲情大门,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这封问亲信,整整过了五十来天,与其说因为她在十五年来从北碚托儿所任教,到目前在一家乡村医院接受监督劳动,需要辗转传递,还不如说,经过了多部门折信检查层层审阅,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医院的门房叫住了母亲,说有一封从西昌寄给她的信。
咋闻西昌来信,她心中一惊,自1967年小儿子失踪后,已整整六年,她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从1966年文革以来,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托过希望的,她年青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们,突然好像从大陆这片海裳叶上消失了,从此再没人给她写信,使她隐约感到,当年学生时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
那么,现在又是谁从西昌给她寄来了久久盼望的信呢?
当她急忙来到门房,从小张手里接过这一封腊黄的信时,她心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预感,“莫非小儿子方兴有了消息”?当她注意那信封被人折开过好几次,有的地方已经撕破,她也只能坦然相对。
其实自己已没有什么值得当局神经过敏的。这么多年来地处北碚边沿的小镇医院,被强迫监督劳动的母亲,对所受的人身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习以为常。她的家已被查抄过十几次了,“革命”群众搜去了他所有稍稍值钱的物品,连一身像样的防寒棉衣都没有给她留下。
前年就为给自己缝一件蘌寒棉衣,招来一顿毒打和斗争,使她断绝了生活的念头,那次她烧掉了珍藏三十多年的老照片,并且决心投湖自杀。
然而苍天却安排了她绝处逢生,她被救生还,并在附近农民们的安排下,一个小女孩在她的身边伴她聊渡晚年……
然而此刻他来不及思考得太多,捏在手里的信封上所写收信地址,分明是:北碚机关托儿所,那字迹好熟悉。她的心紧张起来,立刻又去看那信封上所留下寄信人的地址:西昌909信箱,邮戳上印着:西昌盐源。这会是谁呢?她连忙拆开了信封,拿着信笺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这称谓使她从一场恶梦中惊醒,从她那昏花眼睛里闪出了一束十几年从末有过的喜悦来,难道是失踪六年的兴儿?兴儿,你在哪里?你真还在人间吗?这么长的时间妈为你流过多少泪?你可把妈想坏了呀……
一股暖流溶进了她身上的每根血管,纵使枯木逢春老树新芽,好比行进在沙漠上快要渴死的探险者,忽然发现了一缕清澈的甘泉;一个深埋在地底下将要绝命的矿工,触到了救援者的手,那惊喜和绝处逢生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千头万绪般钻动在心头!
儿哇,你可知道妈妈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一阵激动的初潮拂过心头后,她又从新在老花眼镜背后去分辨那熟悉的字体,写在那发黄信笺上的就这么短短几句话,信的落款是孔令平。
再翻看那信封的背后写着这孩子嘱咐邮递员的话:“邮递员,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已调往他处,请务必将这封信转到她现在的单位上去。”
现在终于明白了,含愤断绝音信整整十五年的大孩子此刻现身了!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廿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孩子呀,这么长岁月你到哪里去了呀,你可知道这十五年来,我怎么盼你的音信?然而每次都在黄昏之后,失望的望着街灯。你的外婆哭过不知多少次了,直到她临终还不停喊你的名字呀!而我熬过了多少断肠的长夜,有过万千次祈祷么?
唉!我的孩子呀,你纵有再大的冤屈和难言苦衷,也该托梦向你的妈妈报一个吉凶吧,然而你却一点声息都没有。
在那个时侯,为娘的也身遭劫难,我因禁锢之身又不敢多打听,写信去重大问到你的下落时,他们从不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
从此生死两茫茫,直到今天,你才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向我喊道:妈妈,我在这儿呢”
天哪!这是真的吗,这是我在做梦,还是苍天安排的悲剧呢?如果这是一场悲剧,那么这是多么残酷的悲剧?这整整十五年来,我的泪水都已经哭干了啊!
母亲连忙找来了放大镜,又拿起那个腊黄的信封反复看那邮戳,再一次证实是西昌盐源县发来的,她又拿起信笺—–是大孩子的亲笔手迹,一点都没有错啊,十五年了,连这么熟悉的笔迹,竟一时想不起来了。
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唉!真的老了,没用了!她把那腊黄的信,摆在小桌上,好久才回过神来,将那腊黄的信收折好,再将它放在自己的枕下。
此时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孩,正挨着母亲身旁。这就是两年前一位附近农妇送来的‘干女儿’。此时她正瞪着那童贞稚气的眼睛望着她。
她认识方兴哥哥,不过那时她仅只有两岁,只记得他长得很高很瘦,但为什么突然走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回到母亲居住的小屋子来?
一切都怪怪的,小脑筋里盘旋着一连串疑问:妈妈是那么善良,她成天为医院打扫清洁,不像其它人偷奸耍滑,医院把所有的重活和脏活都扔给她,而医院的人为什么总是找岔欺侮她?为什么妈妈在忍受人们欺侮时,总是低着头,好像医院里有一根令她无法解脱的绳子,牢牢捆着她?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这么高兴,她注意老人的一举一动,数着她戴了几次老花眼镜,一会儿取出那腊黄的信封,看看又放回原处,虽然她什么也不懂,但为母亲难得的高兴而高兴。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哥哥,他可是在她还没生下来时,便离家出走的,妈妈从没有讲过的啊!他长得像什么样子?她只能依凭她所见到的方兴哥哥的照片,想一付很大很大的图象。
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听说在重庆大学念书时就离开家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离家这么多年从没回过家呢?今天又怎么知道妈妈在这里?
她那小脑袋瓜里翻滚着一连串的疑问,看妈妈在她布满皱纹的鬓角边扑刷刷流下的泪,心里猜测着,这大哥哥什么时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妈妈不喜欢打断她的思考,就是问她,她也不会回答你的。
晚饭以后她躺在小床上,盯着妈妈从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腊黄的信,然后戴上她那付老花眼镜,在电灯下面从新细细读起来,仿佛那信写得好长好长,一直就没有读完似的,一边读,一边又在擦着眼泪。
妈妈为什么还在伤心呢?大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她想着想着闭上了眼睛,去了她的梦乡。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告梦见之。梦见在我傍,思觉在他乡。”(乐府)
这一夜是多么寻常的一夜,母亲望着身边已沉沉睡去的小女儿,她没有睡意也无法入睡,他得马上去找回这个失散了十五年的孩子,最好此时,她能插上翅膀,腾空飞去……但望断茫茫华夏,他在那里呢?
想到这里,于是翻身下床,去抽屉里寻找出那本很旧的地图,这还是兴儿的遗物,在方兴出走时她就反复地看那本地图,想从那地图上找到孩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地图上没有一丝孩子出走的痕迹。
现在有了:西昌盐源。在模糊的老花眼镜后面,她终于找倒了那个位于她所在位置西南方向,相距她足有千公里的盐源县。
凭着她的灵感,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崴崴耸山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服刑役,她得马上给她写信。
于是她伏在小桌上,开始提起笔来,但是千头万绪如乱麻股的脑子里,怎么开这封信的头?第一封信中该告诉他什么呢?
手上的那张信纸,柔了又写,写了又柔。
她知道自己和儿子今天的处境都很危险,纵有千言万语,也是万万不能在信上倾泻的,她知道所有信件都要被对方监督的人拆开检查,寻找“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的线索,于是,这封信便这样写道:
“亲爱的平儿:从我收到了你的信后,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从新获得了我心爱的儿子,便全身有劲。热烈地渴望着有一天我们能母子见面,我仔细地翻阅了地图,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边区,离我这里很远很远。但我的一颗心离你是那么的贴近……”
“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于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又下放工厂车间劳动,1962年调到蔡家场这家医院,1961年11月8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临死那几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死前她一直喊唤着你的名字!
“弟弟于1959年在四十四中毕业,考入重庆电力学校,62年压缩回家,一直跟着我,64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落户在我附近的一个社员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处,生活尚好,文化大革命他瞒着我,于1967年7月14日离开了我,从此音信全无,生死不明。
“我在这所医院整整十二年了,这所医院离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车不到一小时。规模不大,是综合性医院,附照片一张,你妈妈已经老了,希望你也能给我一张像片,要说的话很多,下次再谈。”
这便是一个在遭到家破人亡后的母亲,同阔别十五年沉沦监狱的唯一儿子写的第一封信,那中间被压仰得喘不过气来的辛酸,只能‘领会’。
她知道,要把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诉天涯一角的孩子,又让当局放过它,必得写些中共强迫人们说的“话”。
她微微闭上了眼,想到在中共建国的二十三年中,自己同丈夫,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平常百姓之家,就因丈夫的历史“罪”,不但他本人入狱至今不知生死,母亲在忧愤和潦倒中去世,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在“劳改”,一个生死不明。自己孤伶伶一人被医院的造反派任意践踏侮辱,这究竟是为那门?
而今大孩子居然还在人间,就算一种最大的“快慰”了。唉!这种遭遇岂可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啊?
她从新望了望那张刚刚才写完的信。拿起那破藤椅上的棉垫子靠在小女儿身边躺下,此刻脑海里再次回到十五年前,脑子里全是大儿子的音容。可惜,照片已经完全烧掉了,敞若不是那杨婆婆,自己早成了池塘里的水鬼,这个家就算无声无息在暴政下消失了。
现在想来,杨婆婆的话果然没错,她那时就劝过自己,“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多的是。凭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就不能长着眼睛看看这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那话里可是一种预言,一种普通老百姓在黑暗中的等待,一种希望啊!
她想着想着,脑海子里又呈现出大孩子的样子,活鲜鲜的,宽大而长园的脸旦,白皙的皮肤,从淘气的童年直到中学时代……背着背兜捡二煤炭的身影,晚上伏灯读书的身影,又重新回到眼前。
记得他考上大学离家时,几乎整整一夜同儿子促膝交心,谆谆劝导他:“千万不要去从政,那是一个说不清的危险领域;也千万不要去从事教育,你父亲就是一个活的教训。你选择了工科,有一门专长就是自己一生一世安身立命的本钱了。”这可是父母从动荡的年代里,为躲避暴政总结出的切身体验。
可惜,这样的躲避,依然没有躲过劫难。为什么中共连这么一个勤奋苦读的孩子也不肯放过啊?
想到这里她痛苦地翻了一个身,于是又想到自己同大陆上受残害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自己又招惹谁使她家破人亡?想到这里,她只能打住了,唉!今晚被那些痛苦思绪扰得乱麻一团,总是高兴不起来。
“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州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古人的灾难有今天这么沉重么?
渐渐地,她在朦胧中感应到自己的骨肉,正在无数大山相隔的那一面向她呼唤,于是她真的腾空飞起来了,穿越那重峦叠障的山脉,在那雾气缭绕的冯虚之境,她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孩子,他褴褛一身,瘦骨凌峋。不过那一刻,扑进她怀里的依然是那又长又园像鸡蛋一样白净的脸……
记忆可真是一个怪东西,十五年过去了,处境限涩,音容依旧,就这样母子相逢在梦中,相拥在幻境。醒来时,泪水浸湿了一片枕头和被盖。她望了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儿,替她盖好露出被外的手脚低声叹了一口气。
当这一封信从何庆云的手中交给我时,他那脸上堆着一脸奸诈的笑。
“现在,你总找到精神寄托了吧!你看你的母亲还健在,她可不像你处处同政府对立,你可要好好读读她的来信,不辜负她对你的希望。”他说着,把信交给我。到此时我们母子断绝了十五年的联系,终于接上了,不过十五年前那时,负气天真的想法,已被十五年的折磨彻底纠正,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牵挂的亲人除了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欲哭无泪,断肠天涯。
从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断,因为长期无人照料,饥饿年代死于营养严重不足,而我的可怜的弟弟,真想不到会惨死在造反派的乱枪之下。我又回想起当年小龙坎的夜。我真没有想到我和他共进的那一顿年夜饭,竟是和他共进的最后晚餐。临别时没有遗留下一张照片,我那断肠的追念又向谁表达?
母亲有了下落,我该向她简单讲一下我这几年来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监狱的概况。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所在单位掌权的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无视公民通迅自由的法律规定,把我们的信件私下拆阅,还因为这些小痞子为表现自己的政治嗅觉灵敏,而把信中他们所不认识的字句和不懂的词语,拿来集体“破译”,对信中用到“亡羊补牢”,“扑朔迷离”等辞句,整整研究了一个上午。
他们为此专门找来新华词典,按照那些词的字面解释,一面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点逐一分析,把亡羊补牢说成是我想待机逃出牢房,把“负荆请罪”说成拿起杖棍毁灭罪证,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以后,还要责令母亲作出解释。
可笑的是他们竟会以蔡家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盐源农场的革命委员会写来一封信,要求盐源农场对我严加追查和管教。
在接到母亲下一封回信时,要我写信中不要用成语。
哭笑不得之余,我只好用常人写信的四段式,即称呼、问好、说事、祝身体健康。这大概就是文革对社会改造的一大成果吧!
从那以后,远在千里外的我,算是结束了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孤独,每逢过年过节不再独唱悲歌。还能同其它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样,收到一小包慈母一针一线缝好,熨上她体温和关爱“礼物”。
她把省吃俭用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儿子身上穿的背心,脚上穿的鞋,洗脸用的毛巾,以及粮票。
我知道在这物质极溃乏的年代,寄来的东西来之不易啊!在那一小块肉,一截香肠,一包水果糖中凝聚了多少深情。!
这一年秋收季节,我在山上那些烂在地里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许多白瓜子,把它们洗净晒干,用晚上学习时间,倦缩在屋角落,一颗一颗地剥出它们的仁,再用一块毛巾缝成一个口袋装好,准备找机会带给她。
(二)一包砍皮瓜子
第二年,刚刚刑满的王大炳,回长寿探亲。我便委托他在途经北碚时将瓜仁带给母亲,并拜托他,把母亲生活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1974年冬天,王大炳在阔别重庆整整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到重庆,并且专程沿途询问,找到了北碚蔡家场东方红人民医院,然而,他还没有进入这家乡村医院的大门,便被传达室里的“门卫”截住了。
“你找谁?”那门卫从黑洞洞的窗口里,向外上下打量着这个农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们有一叫方坚志的吗?我是来给她捎信的。”大炳直言寻找的人。
“你是从那里来的,找她干什么?”门卫死死盯着来人,好象要从来人身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大炳好象一个被盘查的人,一身都感到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就像一个隔世的来者到了一个令他恐惧的环境中,他犹豫了一下,只好将我托他带给母亲的信,一包瓜子仁拿了出来。一面恳求他说:“我是从西昌盐源来的,是方坚志儿子的朋友。这次因为回家探亲,受他的嘱托给他母亲带来一包东西和一封信,拜托你是否能通告一声。”
门卫把信和毛巾包接了过去,掂了又掂,满不在乎回答道:“那么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说罢,转身进去。
不一会,便走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向他喊道:“你要见的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重点监督对象,任何没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不能同她单独见面,我已请示了领导,你带来的信和东西,我们可以代她收下,并且转交给她本人,你走吧。”
这闭门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向门内窥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医院么?里面的过道上穿梭着赤脚的普通农民病员。
心中暗暗后悔,如果不去门房打听,径直走了进去,说不定根本没人问他是什么人,今天自己找了麻烦,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看来,今天这么大老远的来,母亲是看不见了。如此看来,母亲的处境,十分不妙。
当大炳回到盐源,把蔡家医院所见情况告诉了我,顿时对母亲的担忧压在我的心头。她在信中不厌其烦的写道“要听党的话”,恰恰证明她是多么无奈,母亲所受的精神压力,超过生活在枪杆子下面的我。
这一年春节,我照样收到了她寄来的一斤猪肉,并在信中告诉我,我给他带的东西已经收到。一再要求我能将半身的近照寄给她。
在狱中,我们的像片一直由当局摄制。所以,母亲这小小的心愿,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我,还真成了一件大难事。我的身边已有十多年没有保存过一张像片了。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一直在寻找去盐源的机会。
盐源地处云贵川高原,在这个汉、彝、藏、苗等民族杂居的地方,有广阔的牧场,放牧的牛羊群,和过路畜群,撒在这一带草地上的牛羊粪一直被农场各队争抢。徐世奎也不示弱,在春耕栽插完毕后,便派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小组,长期驻外拣粪。
这个小组在马路边租了一间公社的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里面,每天所拣的牛粪便堆积在屋外马路边,等到凑足了可以用解放牌拉上几车的数量后,便临时从场部抽调汽车,再派两个人跟着汽车一起到积肥的地点为汽车装牛粪,当时装粪的人一般指派菜蔬组的人。
(三)照像的见闻
当我和肖弟良接到装粪的“指派”后,在我的衣服包里,把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服翻了出来。
在狱中大家都一样,劳动时穿什么,并不感到衣衫褴褛的羞涩。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光头犯人像,我向陈孝虞借了他的呢帽,就这样,把衣服和帽子包好,匆匆到场部汽车队上了汽车。
汽车开抵目的地大约是上午十点钟了,为了腾出照像时间,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车装满,估计汽车往返至少需两个小时,就抽这段时间,汽车开走后,洗了手脚,换上中山服,我俩便向盐源县城中心走去,这是我来盐源十年来,第一次“自由”上街。
盐源就只有纵横交叉成十字的两条街,那天显得很冷清。因为一心想寻找照相馆,并没有过多留意街上的市容。
不多一会,我们就在一家临街小店门口,看到悬挂在街边的照片剧照。走进去,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起身向我们打招呼。问我照的几寸,便吩咐我在一张长木凳子上坐下,没到五分钟,我的尊容便掇了下来。
开票的是一个老者,他向我询问道:“听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们是临时到这儿来出差的吧?”我含糊应了一句,没有在意他对我们的关注。
像照完了,身上感到发冷,便取随身带的“铠甲”披在身上,没想到那老者立即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披在我身上的可是一件全身上下,沾满牛粪的吊巾吊挂“体无完肤”的烂油渣。
这些年老百姓虽然也穿得破破烂烂,但毕竟还没有烂到这样程度,加上“铠甲”散发出来的臭气,使那位老者立刻判断出我们的身份。
他当即表示,我所照的像片不能取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和老肖费了足足半小时的口舌,我还掏出了母亲给我的信,向他说明我照相的来由,好说歹说最后店主人答应,要我必须一周内来取像片,不准取走底片。
真想不到“劳改”连自己照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想不到这么一件“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致惹出麻烦来,也罢,比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来,我虽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万巴衣”游一下盐源街头!
便大摇大摆的敞开破“铠甲”,向前走去。只觉得那上面数十块破棉絮和破布条随风飘摆动,扑扑作响,衣服上粪便臭味也随风散发,使我一时获得那济公活佛的潇洒感。
马路渐渐变得干净起来,左手隔马路大约十公尺地方,出现了一排围墙。前面斜放着两个很宽的玻璃厨窗,厨窗上的玻璃剩下几块残片,那里面贴着许多“文章”。
左面厨窗里,彩色的刊头上贴着:“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十个大字,右面厨窗贴着“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八个醒目大字。
厨窗间夹着宽大约十米的水泥过道,是学校校门。校门右侧墙柱上挂着“盐源中学”四个大字的木板校牌。
到盐源整整十年,只听说盐源中学是盐源县唯一一所完中,也是这个县的最高学府。虽经文革血洗,横扫牛鬼蛇神弄得它面目全非,但此时校门很安静,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进出。
校门口的屏风墙挡住了我们向内窥探的视线,正好,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子,从屏风右侧闪身出来。我忙向他问道:“你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么?”他诧异地望着我,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露出一种不知如何回答的神色,便匆匆走进那“屏风”消失了。
我实在想看一下,文革以来学校被红卫兵整治得怎么样了?正想向里面走去,但又自觉不妥,自己这付尊容,冒冒失失往里撞,倘若被红卫兵拦住,找我的麻烦,我该怎么说?于是收住了脚步。
这些年,六队收纳了一些从文革沙场上扫进来的学生“另类”,从他们口里知道,在学校里,上了年纪的教师除逃亡在外不知去向的,留在校内低头苟且渡日的“良民”,其状况并不比五类好。
校园成了革命闯将的习武场,十三四岁的毛孩子,个个都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使枪弄棒的“红小兵”。
我的目光集中到校门两边玻璃厨窗内贴出的“文章”上。这是些字迹潦乱,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杰作。
好半天我才读出,两个厨窗里虽有“坚决把复课闹革命进行到底”的承诺,但许多“纸”上写着“打倒×××小爬虫”,留着文革年代的野蛮味。
好在在“文斗”约束下,只保持着口头上的“杀气”,并没有血迹。
我极想去看看那屏风后面在演“什么戏”,便同肖弟良商量道:“你想进去看看吗?”老肖露出犹豫的面色,忽然屏风后传来一声大喝“干什么的?”那口气显然冲着我们在问。
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定晴一看,原来是一个年龄比刚才那孩子还要小的孩子。不过,他身着草绿军装,正站在校门中间叉着腰,双眼雄视着我俩,显得幼稚又野蛮。
我原想以交朋友的心态同这些孩子们谈心的,但看到面前这孩子那威风凛凛的样子,使我原先已堆在舌尖上的话,倒了一个拐,全部的吞回肚里去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怎么,不可以参观一下么?同志”。
那小孩居然悖然大怒,挑畔的喊道:“谁是你的同志,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该不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吧!”
糟糕!我们的衣着成了我们身份的标记,在盐源城里,让这些孩子们都能认出来。我和老肖会意地相对一视,此刻我再不想像潇洒的济公,萌生对校园怀旧和好奇心了。
但我们今天招惹谁呢?难道就因为我们的形像也犯了王法?使那男孩用这种口气训斥我们?想到这里,便板起脸,俨然以长辈的口气训斥道:“小朋友,说话要讲礼貌,不要让别人听到像没有受过家教似的。”
那孩子看我们不但没有被他吓走,反而还教训他,立刻更凶恶地吼道:“你们再不走,我就喊人了。”看来,这里是进不去了。
争吵声很快把校园里的学生们吸引过来,屏风后面转出来了五六个脑袋,年龄基本上是十五六岁,一齐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听得他们窃窃私语议论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盐源农场的犯人。”
两个女孩子向男孩嘀咕了一阵,回过身便朝我们喊道:“你们赶快走吧?”老肖拉着我的袖子,暗示着犯不着同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称狠。
面对着这种被人赶出来的尴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悻悻离开了那校门,老肖向我解释:“现在这些孩子,我们惹不起,我们的身份不同,本来今天上街又没向队长报告,出了事还不是由自已负责,何必同这些孩子一般见识。”
学校没看成,反而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一面向着那装牛粪的地方大步走去,任那风吹破棉甲发出的拍拍的响声,一面心里还在消化今天一天的不愉快,咀嚼在像馆里受到的冷遇,和在学校门口的闭门羹。
这一天,我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在这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土上,不但看到它极其贫穷,更体会了它精神的极度空虚。如此在中共禁锁下封闭的社会,如何去面对一个文明世界敞开的大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