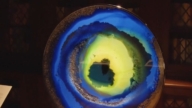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9月19日讯】 居于“天下之中”的国家 2009 年我去日本访问,读到日本外务省前任发言人写的一本关于中日关系的小册子,其中引述日本学界对近代以来日本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战争的一种观点,说是日本之所以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实际上是受了一种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中国文化因素在日本被称为“中华思想”。
作为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我被这种古怪的观点搞得一头雾水。“中华思想”?这个词汇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虽然“中华”和“思想”在中国社会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但是这两个名词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名词,怎么看都觉得匪夷所思,难以接受。
但是,这个“中华思想”在日本学界显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像是今天的日本学者为了为上个世纪的国家侵略行为辩护而生搬硬造出来的。因此,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日本的这位外交官并没有特意做词义的解释。
“中华思想”导致日本人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这种说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陌生,简直就是一种侮辱。这就好比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打人者对被打者说:我之所以打你,是因为我受了你的影响。
看上去,这是地地道道的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
对于这种不中听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搭理它,当它根本不存在。我想,我之所以在去日本访问之前没有听说过“中华思想”这个名词,并不是它在日本不存在,而是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对这个名词的存在视而不见。
当然,这也是最愚蠢的办法。因为已经存在的事物不会因为你的刻意回避而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
那么,这个在日本学界流行的“中华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怎么能够成为某些日本学者眼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殖民战争的思想依据呢?
这要从生活在亚洲大陆中心的人类在远古时期凝聚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开始探究。这个过程发生的时间点,大约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大概距今天4000年至5000年左右。对应的政治年代,应该就是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已经露出痕迹的“夏”朝乃至夏朝之前的颛顼时代。
那时的人们显然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成熟度的显性表征就是人们的敬畏感。在这个星球上,无论在哪个区域,人们最初的敬畏对象都是“天”。如果说“天”是一种客观称谓,那么“上帝”就是“天”的主格名词。
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汉语的“上帝”这个名词并不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源于中国上古,在中国的传世古籍《尚书》乃至更早的典册中屡有出现。只不过,由于中国的“天”信仰早就被历代最高统治者所垄断,中国普通百姓没有权利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汉语“上帝”一词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乃至于在近代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土之后,被西方教派所借用,从而与中国本土信仰疏远开来。
“天”是高高在上的,有上就有下,“天”的下方是人间,也就是“天下”。而“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也就是“天”的儿子——“天子”,“天子”理所当然地居于“天下之中”,由“天子”所直接统治的位于“天下之中”的领域,就是“中国”。在“中国”的四周,则是“四夷”,具体的表述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夏”虽然最早是季节名词,但从词源上说,“下”与“夏”是相通的。只不过,“下”乃单纯的对应“上”的“下”,而“夏”则是专指“天下之中”的“夏”。“夏”字的结构,上是“一”代表天,中是“日”代表悬在天上的太阳,下面的“手”当然是人之手,代表正在劳动的人。上有“天”,中有“日”,下有人。天下之中,上下贯通,此为“夏”,也就是中国。此“夏”也是季节之“夏”,夏季阳光普照,万木生长,百花盛开,是距离“天”和太阳最近的季节,当然也是代表着“天下之中”的季节。“华”者花之众也,百花之繁茂状也。万木葱茏、百花繁茂之“天下之中”即“华夏”之意。“华夏”之尊,由此表述无遗。
统治着“天下之中”的“天子”,由于专享礼祀于“天”的权利,则成为“天”在人间的唯一直接代理人,也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他所统治的生活于“天下之中”的臣民,同样也是天下最尊贵的臣民。对于唯一受“天”眷顾的“天子”和他的臣民来说,周围四夷的存在价值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四夷都是些野蛮人,是介乎于兽与人之间的生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夷的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居于“天下之中”的“天子”和他的臣民的利益。同理,为了居于“天下之中”的天子和他的臣民的需要,去征服和压迫四夷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这就是《左传》所载西周王朝的统治伦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天下之中”的概念与实际的地理位置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相互比较之下的地域文明成熟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从现代考古发现的成果来看,在距今5000年到 4000年之间,亚洲大陆的东侧靠近太平洋的广大地域内,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继或交错达到成熟期,在改革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的一定盈余,其显着特征是文字的系统化和酿酒工艺的成熟,这对于祭祀仪式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神秘的发展过程是一次阶段性的推动,产生了包括巫史吟诵、鲜花簇拥、美酒祭奠的酒礼文化。这是人类农业文明的第一个成熟期。创造了这一农业文明初级阶段成熟的人们被酒礼文化凝聚起来,形成国家的雏形,并把这个初级国家命名为“华夏”。由于他们与“天”的特殊关系,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天下之中”,“中原”和“中国”的政治地理概念由此而产生。相对于处在农业文明之外的“四夷”之居民,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是不证自明的。
当然,文明的优越感以及“天下之中”的统治者的伦理逻辑是一回事,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自从在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华夏民族的认同感之上建立了“中国”之后,物质相对富饶的农业“中国”与物质相对贫乏的北狄与西戎(东夷已渐次与中原文明融合,南蛮则有广阔的气候湿热、自然物产丰富的丛林湖泊可以求生)之间的相互冲突就成为贯穿几千年历史的一大主题。冲突的双方虽然各有优势可恃,但从中原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戎和北狄往往扮演着侵犯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约公元前700年以后,中国西北的游牧文明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发展,相对于中原农业文明,西戎和北狄开始建立起了战争工具的优势(胡服骑射),中原各国被迫修筑土墙(长城)进行防御,双方在冲突中的进攻优势更多地被游牧民族所把握。秦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秦国统治者深厚的西戎文化背景。
汉唐中央帝国的建立代表着人类农业文明鼎盛期的到来。在这两个帝国统治期间(约公元前100年——公元600年),中原农业文明在与西北游牧文明的战争博弈中在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优势地位,从而也巩固了中华文明的在“天下之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优越感。在汉唐中央帝国的君臣看来,所有中央帝国之外存在的政权无非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需要被征服或驱逐的番奴之邦,一种是对中央帝国倾心纳贡的属国。实际上,中央帝国周遭的政权形态更多时候是摇摆在以上两种类型之间,与中央帝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时战时和。结果,汉帝国收服了北部边疆的南匈奴国,并把桀骜不驯的北匈奴国驱逐出北部草原,把他们赶到了欧洲(从语种上考察,今天的匈牙利人、芬兰人均具有匈奴人的遗传基因)。在征服匈奴的同时,汉帝国还收服了西域的众多小国,迫使他们成为中央帝国的附属国。唐帝国对于崛起于北部草原的突厥国家采取了汉帝国对匈奴国同样的强硬政策,迫使突厥人沿着北匈奴逃窜的路线向西方迁徙(今天的土耳其人、中亚人以及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都有突厥人的血统)。与此同时,中央帝国对越南、朝鲜半岛的征服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强大文明影响所及,远至整个东南亚和日本岛上的倭国。
可以看出,汉唐时代的中央帝国是具有明显的扩张性质的国家。作为农业文明的最高国家形式,汉唐中央帝国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对匈奴、突厥的战争是为因游牧民族不断寇边而引发的自卫战争,开拓西域亦是为了制约匈奴),也是为了维护“天”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天子”以及居于“天下之中”国家的尊严(对越南、朝鲜均是如此)。因此,这种国家扩张行为的边界是很清晰的,一旦自身安全和尊严受到切实的保护和尊敬,扩张行为也就即刻停止。这与工业文明的代表国家——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帝国为了市场和资源在全球进行的没有边界、无休无止的扩张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区别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是两种文明的不同需求所决定的,而不是东方黄种人与西方白种人之间的人性区别。
唐代之后,居于“天下之中”中央帝国的扩张行为基本上消失了(蒙古游牧文明的扩张行为属于另外一个讨论专题),但是文化心理上的“天下至尊”心态却历尽艰难与屈辱而得以顽强保存。在1840年之前,包括越南、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行为虽时有中断,但作为东亚国家之间的一种国际制度却一直得到承认和保持。
在作了以上简单的历史梳理之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工业文明进入亚洲之前,作为人类农业文明的杰出代表国家,中国乃至华夏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于东亚诸国的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实的代表着最高价值(天)、居于天下(东亚)之中的中央帝国。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