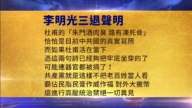【新唐人2009年9月18日讯】2004年11月,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对于中国,如同在红色恐怖的乌云间,绽放出预示着正义和力量的曙光,从此,中国的历史走入了解体中共,复兴中华民族的进程。
那时,我刚刚踏上自由的国土3个月,第一次读到九评时内心深深的被震撼,九评是对中共最深刻最详尽的剖析。5年来,我不知读过、听过九评多少次,思想也随之净化,回归一个真正中国人应有的思维。
暴力是中共制造恐惧、控制民众的手段
2002年1月4日下午,在这个咋暖还寒的冬日,我因为在北京街头散发揭露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传单而被三个便衣以暴力手段非法绑架。我努力挣脱他们的扭拽并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三个男人在闹市的众目睽睽之下,拚命的往地下按我的脖子,还试图堵上我的嘴。之后从下午2点一直站到半夜12点,我被关在派出所里仅容一个人能够站立的铁笼子中,至此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是一场十足的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绑架。
2周后,海淀分局看守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小队成员,警察朱锋、薛绍康、杜崇等5人,把我上着手铐塞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劫持到一个洗脑班。在那里,一共有12个警察、保安和他们指使的打手帮教。他们不许我睡觉,不让我站着、坐着,只许蹲着,还得抱头低首的姿势,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向我灌输中共诽谤法轮功的谎言。我拒绝这一切,他们就扑上来打我。其间,我来例假,他们一如既往的折磨我,而且还加上3条新的要求:限制喝水,限制上厕所,绝对不许我用卫生巾。当血湿透了我的裤子,他们又破口大骂我是流氓、在男性面前这个样子以及弄脏了他们这个地方等等。他们的言行和思维无耻到了不能用“流氓”这个词的正常含义来形容,是为了到达自己的目的丧失一切道德底线。几个月后,我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中听到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说“中共是一个大流氓,把他手下的人都变成一个个的小流氓”。我想,每个从这个邪恶迫害中走过来的人,只要他还保存一点点善良,他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在那里我第一次被警察打。那是在一个深夜,当我再次严词拒绝了签字放弃信仰“真善忍”之后,年轻的警察杜崇在海分看守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小队长朱锋的授意下,对我开始使用暴力。与此同时,朱锋在旁边咆哮着恐吓我“你要不写,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撅断!我一壶开水浇下去不把你烫熟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当我真切的感到杜崇的第一下重击时,我的反应竟是不顾疼痛、扭过头回身去看他!因为我正在经历的和我20多年所受到的中共的灌输截然不同:在我1992年离开中国去海外留学之前,我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说这个党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警察是保卫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等这样冠冕堂皇的政治宣传。所以,在那一瞬间,我头脑里如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中共的一切灌输在我脑子里都雪崩一般彻底崩溃。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再也不信中共的一切鬼话。对于中共,我当时能认识到的是:这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这个理智的选择保证了我在这之后2年里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能不断磨砺坚韧,回归善良和正义。在这个洗脑班中,当我不知道如何逾越这非人的虐待时,我曾签字不炼功,这虽然不是我内心真实的意愿,却作为我人生的耻辱给我精神上带来巨大的痛苦。
当我日后看过九评后,曾仔细的回想过我们家在三代以内所有我认识的亲戚中,有多少受到过中共的残酷折磨,结果把我大大的震惊了:我的祖父因为在5、60年代因为几句真话被剥夺了在沈阳财经大学讲课的权利,而被打成“右派”,全家老小都被遣送回湖北农村种地改造,我的叔叔、姑姑在以后一生中的升学、工作、结婚、住房等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刁难,以至各种人为的折磨。我母亲姐妹4人,我的大姨夫因为留学日本被批斗,然后被强制去种地,就在大姨夫病得无法走路只能爬行的时候,还被逼继续劳动改造。最后40岁出头病死在田间。大姨被从讲台上赶到煤矿里去干苦工,后来在事故中留下终身残疾,几十年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我的二姨夫因为耿直的脾气得罪了领导,多年都是被批斗整肃的对像,这种来自整个社会的强大压力对他的精神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到他晚年时,只要一喝酒就像孩子般大哭,讲诉他无尽的委屈。我的三姨夫被政治运动中承受不住的熟人诬陷,从而无辜却遭受疯狂的迫害,38岁在肝癌的剧痛中撇下我三姨和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人世,三姨后来精神失常。我父亲因为寄钱赡养没有经济来源的祖父而被认为和右派父亲不能划清界限,并且因为他被公派留苏获得过博士学位而被当作“臭老九”批斗,在我出生前19天,我母亲病到血压高达200多,随时可能死亡。但我父亲和同一单位的许多知识份子被强制押送去农村劳动改造,那天,我13岁和大哥和5岁的二哥在大雪纷飞的盘山公路上追赶着押送我父亲和其他人的大卡车,哭喊着“爸爸,你回来吧,妈妈要死啦”,长达2个多小时,车上的军人持枪看着不许众人落泪。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在1-20年中因为孩子们的不幸遭遇而提心吊胆的活着。我的大哥生下来没多久就赶上大饥荒挨饿,16岁半被剥夺继续上高中的权利,被迫上山下乡去干农活,我二哥89年六四那天夜里被军队用机枪扫射,封锁在天安门附近的小胡同里,因而得以幸存。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二哥因为在海外揭露了中共对我的非法抓捕和对我家的非法抄家,被禁止回国照顾我70高龄的父母亲。在我认识的亲属中竟然没有一家能免于中共的魔掌,中共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中共的谎言最惧怕真相、勇气和理智
我在2000年8月因为在德国公司的工作而回到中国去,那时各种媒体上充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还是谎言,中共在制造谎言的时候从来没有正常估计过人类的正常智力,也从来没逃脱过神必定给人留下真相的安排。它的谎言真是漏洞百出。
2001年1月底,“殃视”热播“自焚”伪案,企图把全国老百姓都掩埋在对法轮功的仇恨之中。2月的一天,一生行医的母亲问我说,那个在“自焚”中着了火后还能大声喊叫的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着火后身体周围的空气被加热,人的口腔和呼吸道里面的粘膜比皮肤还敏感脆弱,所以马上就会被灼伤,根本不可能声若洪钟的大喊,这是医学常识。我于是拿出法轮功的书来给家里人看,上面明确写着正法修炼绝对不能杀生。
接下来,京城又发生轰动一时的傅宜斌杀人案,中共又再次栽赃法轮功。那天,我下班刚回家,不等我开口,家人就来告诉我说,电视上看到傅宜斌说话了,他肯定是疯子,精神不正常。正常人要是杀了人,自己早就吓得六神无主、魂飞魄散,一个小孩子到那时候都能一拎他的脖领子把一个成年的杀人凶手拎得双脚离地,怎么可能对着电视镜头大模大样的说起来没完呢?正是精神病人的表现。事实上,这么多年谁也没见到对傅的判决,也正说明他精神不正常,是不能担当法律责任的。而法轮功要求修炼者都得是头脑清醒的,明明白白修炼升华的。
在我2年被非法关押期间,无论什么时候,我父母问到我的情况,警察都回答说我被照顾得很好,尤其强调他们对待我们的教育是“春风化雨”一般的。2年后我回到家中第一天,家人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整容了吗?”那时,我比被抓前瘦了将近30斤。2年人间地狱的折磨足以使我在亲人眼中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
调遣处的苦役正是这人间地狱的一部分。我在调遣处被迫包筷子,工作平台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床板,被褥卷到一侧,所有人都坐在幼儿园里给小孩子坐的那种很矮的硬塑料椅上,人坐上去之后,整个人连同椅子一同插到床板底下,使得上身只能保持正直。除了去吃饭以外,一天就是这一个姿势,每人每天最少定量6000双,最多一天是每人1万多双。一天少则干12个小时,多则18个小时的干活。下午4点钟到晚上9, 10点之前,那是最累的时候,忍着渴,憋着尿,手上飞快的包,浑身僵硬酸疼,累得头昏脑胀,唯一支撑我的是信仰。因为那时候,我面对警察明确的讲述了我不可能放弃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海分的警察对我迫害后得到的签字正是他们执法犯法的罪证。当时对于我来说,虽然很需要勇气,虽然我很清楚声明之后可能发生的迫害,但说出这句真心话是一个人的良心的最低要求,以前由于做错而产生的内疚、自责、绝望和羞耻都随着坚守道义的行动被荡涤得干干净净。
那时,我已经从警察面对我时的和蔼以及转过脸对待其他学员的咆哮嚎叫中,分析出了海外对我一定有营救。当初,中共刚开始打压法轮功,我们在德国的学员几十人自发前往波恩的中共驻德大使馆去递交请愿信。尽管我们柏林去的车中有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问题,但我们所有人还是坚持挤在一辆车里,终于准时到达。我相信是因为海外公开的营救迫使警察在我面前作秀,也使他们在我声明之后没有像其他没被营救的学员那样被残酷迫害,警察采用了隐蔽而狠毒的手段:我们包的筷子无论是散装的生筷,还是包好了的成品,都是放在箱子里,需要一箱一箱从下一层和我们所在的三楼之间搬运的。在每个班级中,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轮流去把成品筷子一箱一箱的抱到一层,然后把50斤一包的生筷子扛到三楼,渐渐的我发现,在我们班中,只有我被命令去干这个活,别人要去都不让。我明白,警察的毒计是想从体力上累垮我从而逼迫我在精神上屈膝。那时,唯一支持我的是信仰, 我的力量和坚强来自“真善忍”。
为了以后把他们的迫害曝光,我有几天连续计算我当天扛了多少斤筷子,因为箱子上标有公斤数的,生筷一包是50斤。有一天是400多斤,还有一天是700斤左右,还有一天特别累,当我算到超过1000斤的时候,我就不再算下去了,因为那就是个数字而已了,有谁是设身处地理解这数字下的涵义呢。就是那一天,在等候洗漱的时候,我的四肢无法控制的抖动,我感到四肢就像管道一般,一块块能让我很疼的东西从四肢被推出身体,密集程度就好像电影里战争场面中演的大炮在连续发射炮弹一般,晚上睡觉时,累得翻身都拖不动两条腿,因而翻不了身,腿像灌注了水泥一般又硬又沉。就是天天看到我们这样的生存条件和奴工劳动,警察还能告诉我父母他们对待我们是“春风化雨”般的爱护,
中共的谎言不仅在中共泛滥,而且有意识的渗透到海外。2008年夏,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夕,德国黑森州电视台举办一场现场直播的辩论会,主题是在中国目前的人权情况下是否支持北京的奥运?节目编辑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消息,并且公开征集自愿者来作现场观众,这是民主国家很普通的方式,操作非常透明。中共利用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凑足了2-30位控制的华人去报名,其中有4位历届法兰克福市中文学校的校长,从而使得德国电视直播节目的现场直接被中共所操控。表面上,能够在德国观众面前得出符合中共政治需要的结论,影响海外视听,实际上,摄像机忠诚的记录了他们的面孔和言行,将来会成为中共罪行的证据。这是我在第一现场亲眼目睹的。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到达海外后,逐渐听到一个关于我的谣言。谣言说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动手打过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后来这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谣言说我来到海外是给中共当特务的。我第一次听到这话简直觉得是天方夜谭,极其可笑。我想都没想过,更不要说做了。我相信,这个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一定和中共有关。我不会花时间去调查取证,虽然在法律上这是诽谤罪。我非常清楚,就是因为我全力以赴的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触动了它的痛处,所以它们才散布谣言,想把水搅浑,阻碍我去揭露。我既然能认清就决不会上当,所以我从未停止过告诉人们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恶和营救我的同修们。其实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就能看出这个谣言中所包含的中共特色:崇尚暴力的本性、恐吓和挑动仇恨斗争的意图、以及狡诈的掩盖,还有那任何谎言都不可避免的愚蠢的一面。试想:和我同时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三队(而不是四队,那里同时期有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女学员)2年中一共也得有2-300人次的学员,如果真的发生过那样殴打学员的事情,那么多人中怎么没有一个在网上曝光这件事?那揭露迫害的邮件应该像雪片一样多的发到法轮功学员的明慧网上去呀。在劳教所里面那么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把新经文传递到每一个班,所以一切事都是瞒不住的,怎么没有一个人曝光呢?为什么没有来自大陆的确实消息而能在海外传播呢?事实上,中共灌输的党文化思维正是滋生和留存谣言的温床。在党文化的侵蚀下,人们失去了诚实、单纯和善良,猜疑、恶毒和明哲保身倒成为了所谓正常的思维,是人自己迷了眼,回归到善良纯真上,就能有理智有智慧。
无神论不过是中共利用来统治的工具
在中共的宣传中,人对神的信仰被当作迷信来批判,被当作落后、愚昧来嘲笑,进而歪曲到宗教是谋财害命或争夺政权极其可笑的邪理歪说上去了。人看不见神,就说没有神,那只是愚见。但中共却利用无神论去推销它的斗争哲学,改造人们敬天畏神的世界观。否定神的存在,就否定了天国世界,就否定了六道轮回,就否定了人类本身遗失了的本能,否定了生命的意义是要返回先天善良的本性。然而,神无处不在,无时不照看着人类,偶尔也就会给人展示出一线真迹。
我小时候做过一个很奇特的梦,梦里我看到父亲和我在一个叔叔家,屋里很小,让我醒来后最不理解的是他家的一个箱子怎么是挂在墙上的?那时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几年后文革结束,我们全家搬回北京。一天,父亲领我去看他留学时的好友顾叔叔,当时那位叔叔全家三代人挤在几平米的蜗居里,叔叔家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台洗衣机,当时还是很少见呢。因为屋里实在没地方放,这位工科博士自己动手,把洗衣机靠墙吊起来固定住,平时就这么挂着,用时再放下来。日后,在我们全家多次笑谈此事的时候,我才逐步清楚地回忆起我以前在梦里就经历过这一切。青少年时代,我接触了气功之后才明白那是人体的本能——宿命通功能。
修炼文化本是传统文化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是人和神连接的重要纽带。在整个中国社会都被中共宣扬成无神的天下后,修炼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就只能萎缩成了气功祛病健身这么一点点很现实的内容了,但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修炼的经历会留给人说不清楚的对气功的好感和兴趣。
80年代中后期,我和二哥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俩都非常醉心于气功。那时也不懂怎么修炼,但我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却能在夏天坚持静立1-2个小时,以为那就是炼功了。每一次汗水都从肩头一直流到手指尖,再滴落。我至今都记得二哥在上大学以后,在冬天穿着军大衣,带着大皮帽子,一个人坐在街心花园的雪地上打坐到半夜的样子。
90年代中期,我们全家除了母亲都在国外一段时间,母亲那时每天晚上都静心打坐,我回国探亲时她亲口告诉我她在入定后看到了天上的事。她描述得非常详细,尤其是天上要铲除妖孽时要出动多少天兵天将,母亲竟能说出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是我翻遍所有思想的角落也找不出来的。我从小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并且兴趣广泛,尽管如此,母亲所讲的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以非常惊讶、非常不解又非常好奇。
1996年,我在德国读书期间,在寻找生命意义的途中,曾短暂皈依过佛教。在释迦牟尼佛生日那天,法师教我们每个人如何磕头上香捐钱,如何求佛陀保佑发财等。我听了很苦闷,因为那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要什么。等到我跪在佛像前举着香的时候,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捐了钱,求了佛,磕了头,又走了。我跪在那里心里又急又乱,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我不能随便说,我必须说出我真心想要的。突然,我的嘴自己说出一句话: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听到这句话,我整个身体吓得一震,但马上理智就能判断出这正是我所要。于是,我非常开心的“哐哐哐”磕了三个头,然后上香。2个月之后,我得遇法轮大法,从此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路。至今我都深信那是我跪在那里纯净的一念感动了神佛,因此赐予我一个生命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佛法真理。
我在非法被关押期间,非常非常频繁的看到过法轮和七彩的光环、光束,最大的有1/4个天空那么大,也有是整个一面墙那么大的,颜色极其透明,色彩非常美妙。我相信人的一思一念、每个选择神佛都清清楚楚,那殊圣的景像是神佛在爱护和鼓励着受难中的人们。
我看到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多少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欲,害人不知截止,撒谎自以为聪明,违背人伦不知羞耻,我常想: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了对神的敬畏,丧失了善恶是非的标准,才敢这样放纵。人在放纵私欲时,虽然能得到现实中的一点利益或一时的满足,但必定为自己的未来种下痛苦的种子。
中共邪教政府的迫害是在斩断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根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运动最终就是想把中国人在书本里、文物里、脑子里、骨子里的一切传统文化都铲除干净,那样党文化就是人们唯一的指导思想了。古代留下来的真迹被烧掉了,文物被砸烂了,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人被全社会踩在脚下来,人格和尊严被剥光,那么,神传给中国人的正统文化、传统文化就真的能绝迹吗?
我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夕阳下,父亲拉着我的手,在山间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解唐诗、宋诗和古文的含义,一遍遍带着我吟咏和背诵。那是我父亲自己童年在私塾里学到的,他也这样教育我。从那时起,我认识了李白、王维、陶渊明,古人理想的人格和对天地的认识就在合辙押韵的诗句中,潜移默化的容入了我的血液。虽然我出生在文革中期,父母作为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份子极力保护我们孩子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并且高度重视我们的教育。学字使我体会到汉字的美妙,学诗使我理解了汉语的韵律之美,学史使我明白了如何做人。记得每次下山回家前,父亲都会蹲下来,注视着我的眼睛,郑重的告诉我,绝对不能对别人讲学了这些诗。有一次,父亲大概是觉得我能理解得更深,就给我讲了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告诉我什么叫信义,什么叫承诺。
大约76年,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个阿姨来我家借钱。那时全家就只有一间屋子,所以,我看到了整个事情。那个阿姨哭诉他家怎么没钱,孩子们没饭吃。爸爸同意,妈妈就不啃声。直到妈妈气哭了跑出了屋门,爸爸也跟出来,我很害怕就也跟出门。听见妈妈对爸爸哭诉:“你忘了他丈夫是怎么批斗你了,骂你的话根本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就那么羞辱人,看着你干活挑着扁担时都不许你换一下肩膀故意折磨你,你为什么要借给他钱?他们也挣钱,都自己喝酒喝光了,我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呢!”我看到父亲的表情极其痛苦,一直只会喃喃的说:“你想想他们7个孩子,你想想他们的孩子没饭吃”。 我仰着头,看着父母,早已泪流满面,心乱如麻。因为我知道父亲是对的,可我不忍心看母亲这么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父亲递给了那个阿姨20元钱。到我们全家离开西北时没见到他们来还钱,后来彼此再也没有联系。我少年时经常回味这件事情,每次都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能解决?稍微长大一些,我试图寻找父母亲这样做的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善良还有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那是植根于中国千百年来承传下来的正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人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极其扭曲的社会环境中,还能保持着正直、克己、忍让、与人为善的道德操守。
2002年到2004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时候,我父母亲的品行曾经带给我一次更深入的思考。那时,我们无数次被强制去听那些中共用来洗脑的录像带,通常我都会在思想中全力抵制这邪恶的灌输。有一次,我却很反常的抬起头来好好的看,因为那是介绍世界公认的邪教的六大特征,我在心里把我所了解到的中共在方方面面的表现和这六个特征一一详细的对比,最后,我确认中共是符合世界标准的真正的邪教,这是我第一次从理性上认识到这一点,我当时的感受是毫不惊奇,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早已经使我从感性上知道了这一点。当我确认下这个结论时,在我头脑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我父母亲的形象。因为我清楚他们的为人,并且他们那时就是党员。我顿时被憋在两堵对峙的山峰中一般,足足一天半之后,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一切才豁然开朗:我问自己,我的父母亲是因为当了党员之后才品德高尚起来,还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瞬间就明白了,他们的道德标准和做不做党员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才发现入党在中共统治的社会中是生存的办法,我也想起自己高考前学校要求不入团不能毕业,而所有的大陆中国人都是这个邪教政府劫持到手的囚犯。
2004年夏,我从2年的非法关押中回到家中,父母很快就发现我还在修炼法轮功,他们整日为我提心吊胆。一次,我和满面愁容的父亲谈起这事,我告诉他,正是他在我儿时教我的那些古诗古文,才使日后建立了不肯止于世俗的人生方向,以致我日后遇到法轮功时选择了修炼“真善忍”。我问父亲:“如果就因为今天的迫害而要求我放弃,那是不是您在我小时候就教我的那一切都是假的吗?”这话一出口,我真是心如刀绞,忍不住失声痛哭,父亲呻吟般的说出“不是啊!”,也已经是老泪纵横。。。。。。在那一瞬间,我才第一次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去审视中共的罪恶:它真的是在斩断中国人的根,它在斩断中国人一切一切和自己的民族、和神传文化联系的血脉,把中华民族变成虽然保存着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形,灵魂却被掏空、舔食着血腥邪恶的党文化以为美味的精神贱民。它一次次的搞运动就是想抹去中国人对道德和道义的一切认同和记忆,在迫害法轮功中它的邪恶达到了登峰造极,就是因为“真善忍”揭示了更大范围的真理。
如果不是因为神韵演出,我真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如何能从这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中复兴。2008年我看神韵演出时,我记得自己当时真是如痴如醉,神韵的美得令我感慨万千。在那之后大约半年的日子里,我几乎每一天都会回忆不同的节目,细细的品味其中的文化涵义:不在于色彩的瑰丽,不在于天幕的奇绝,不在于穿透云霄的歌声,不在于和谐的乐队,是演出中传达出来的那种韵味,在一举手、一投足里,在一回眸、一展袖中,那才是真正中国人的翩翩风度。那里有真正的中华男子汉的阳刚和忠义,那里有最纯正的华夏女子的温柔和娴淑,神韵中有最美的中国人,有最正的中国文化。那美好、丰富而隽永的意境,让我每次想起都觉得是第一次见到,也永远不想离开。如果说九评如同九把利剑穿透了邪恶赤龙的咽喉,横扫了中共的伪装,使解体中共成为必然,那么在神州大地的文化与精神的废墟上,神韵正在带领着中国人回归艺术和道德的正轨,我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
熊伟
2009年8月27日 写于德国美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