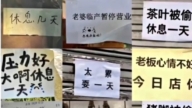一、强权主导下的“围城”中国
钱钟舒先生的《围城》,对城内城外的人与事尽有述说,但从那段历史无法体味当今中国的时代气息和现实脉搏,所以我们不得不另行说一说属于自己的时代。
我们的故事,发生中国这片多变的“热土”之上、游离于改革与革命之间、是活生生的“新鲜货”,皆处于现在进行时,比钱先生的主题更具挑战性和残酷性,故事中的现实,无疑还将是一个让中国时时面对的历史抉择难题。
这个主题当然也是一个悖论,表面上看一方面是“党的恩情似海深”,“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党的惠民政策和亲民举动经常而及时地见诸党媒报端和政要嘴角,甚至媒体镜头前还出现了农家小院和田间地头,意图让农村体味到党的温暖或是威严,一方面却是农民“不知感恩戴德”,仍毅然决然地弃家舍亲,离开养育自己祖祖辈辈的土地而不顾一切地奔向城市做二等流民,让人不明白这又是为何?
进城的流民有打工的,贩卖的,混饭的,坑人的,偷窃的,还有报仇的,上访的,革命的、做梦的,他们的到来使本来平静如死水的城市平添了改革与进步的繁华,有了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本钱,同时也带来了管理上的烦恼和城乡利益的直接冲突,演绎出城市生活中另一道移民“风景线”。
城市享用着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看着不知疲倦、不懂苦脏为何物的现代“工奴”,好像总算在中国人自己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当家做主人的优越感。以工厂为例:长期工盘剥合同工,合同工盘剥昨时工,早就成为一种潜规则,虽然现在这种称呼已经不多,但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其它名称和形势下的身份歧视,如中国的城乡隔离制度(同外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中国却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了,而有权的欺负有钱的,有钱的欺负没钱的,城里的欺负乡下的,从来就被国人视为理所当然并津津乐道。
就在城市享受农村带来的种种无私奉献的同时,看着伴随城市生活而逐渐增多的“外来人”,有时却为“城市生活不太美好”而烦燥,为附带而来的种种不便而心生怨气:本来洁净的街道旁现在这些挥之不去赶之不绝的小商小贩和满地的垃圾遗弃物,附近贫民窑里破落的败象、时不时发生的失窃案和打斗群殴的亚人类生活,一定是这些粗鲁的农村人的先天劣根原罪所致。
因此,城市便利用权贵和小市民的天然联盟所掌握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优势,为这些外来的二等人类进行法律圈定,出台了种种如“暂住证”、“居住证”等身份限制,更配置了“城管”专门对付街道“走鬼”,增强了“保安队”专门对付犯罪,美其名曰“加强管理”,实则是城市大门越关越紧,让那些未进来的望而怯步,已进来的见好就“收”,以图将“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落到市民的生活实处,“让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城市”,进而最好让“没剩余价值”的农民返回乡里,为城市人种地种菜修理“后花园”,做地道的“农奴”才是。
城市生活有时倍感压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时候,城市想到了农村,想起了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中去,去体味田园之乐,去行善人之为,去找艺术的灵感,去看望快被遗忘之人……
当城市人以梦想者、旅游者、旁观者、消费者、事不关己的欣赏者,从遥远的审美角度来审视农村时,农村就是一幅水墨画,农村就是一首田园牧歌,农村的苦难就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农村的生活就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这一切就可以成为文学家笔下的素材,成为摄影家镜前的构图,成为旅游者眼前难得一见的开心果和下饭前的开胃酒,而深在其中“表演”的不再是农民的“旅游业者”,则成为一个个视钱如命的玩偶,在为城市人重复上演着一场场出卖尊严和前途的经济猴戏。
当农民不再种粮,而成为供应城市经济作物的原产区,成为城市调节空气的后花园和精神消遣的附庸;当农村不再臭气熏天,成为不再自然的“油漆绿”,成为城市旅游者“采摘”逗趣的享乐天堂时,这时的农村所得到的一时发展已不再与三农相关,早已归属到所谓的第三产业或是服务业当中去了。—-但旅游业替代不了中国的支柱农业,也无法负担起振兴农村的历史重任,所以没必要为一时之“鸦片”快感而欢呼。
中国是世界垃圾食品的主要生产地也是最大的消费地,中国是世界自然环境被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社会”立行国,而农村因为贫穷,因为弱势,政治上没有公民身份,经济上得不到必要的投入,生存上更处于自生自灭,那里的人们就是这种垃圾食物、垃圾制度和破落环境的最后受害者和买单人。
总之,城市天生就是花钱的地方,是享受生活的地方,是人类梦想成真的地方,农村是保证“生存权”的寄宿地,是下放和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农民天生就是被劳改、就是要想法挣城市人的钱、养着城市人享受的命。这是“城市主人”的制度安排,弱势的农村人有时或许要认“命”,这个“命”,就是“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这个“命”,几十年来一直就这样让农村像祖爷一样尊奉着。
为何农村人都想生活在城市,哪怕是城市的边缘,哪怕做城市的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了呢?农村人说,我们的要求不高,吃饱喝足了就行,再苦再累也不怕,只要不让我们回去;城市人说,农村那么好,那么环保,那么绿色,那么悠闲,那么自然,为何还要来城市与我们争饭呢?
这是一个怪圈,也是一种“围城”现象。
二、给农村活路也是给城市活路
每个中国人都想做城市人,而不愿留守乡村和田园,是因为千百年来的城乡差别和政治歧视所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任何城市人的祖上三五代以内皆来自于农村,都是农民的后代,但做“城市人”这个愿想一旦实现,即自封为不再“农村”的城市人。
战乱的年代,城市人大多会流向农村,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依附于农村,而和平一旦来临,农村的避难作用瞬间消失,城市人则将农村人拒之门外,登高忘祖立刻翻脸不认人,身上所潜伏的那种小农意识、泥土气息马上蜕变成小市民阶级的狭隘市侩气,然后通过改头换面后的“排外拒乡”形式对后来者尽情地表现出来。
现如今风行一时的城市精英落户政策,是对外来人才的一种“恩赐”,名为“吸收人才”,实是在进一步提高进城门槛,是在利用城市的地理优势抽农村和偏远地区发展的“血液”,在用制度“欺负人”,到头来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地区城乡差异越拉越大,矛盾越积越深。
为了安慰部分对政治歧视心生不满的农村人,城市又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如补贴三农,减免税费,低息贷款,家电下乡等,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是治标不治本,城市还是繁华无比,农村却是破败无疑,农民们当然更不领情,失地农民依然外流,城市“外来人”越来越多。—-难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一个让城市人凭空向往而不愿久留,让农村人弃之如鸡肋守之如毒药的怪物?
人与动物一样,是逐食而居的,并且人是要逐好食,居好屋的,所以才有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训示。只要人的本性还在,那人类的自然流动就应当是合乎自然,合情合理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城乡对流现象(其实绝非对流,而是因资源配置不均等,形成了单向流),肯定是我们人类的哪一项或是数项设计安排出现了与自然与现实不相符的地方,比如掌握了立法行政大权的城市,在制定法律和政策上的自私性和倾向性,使社会产生了现实的利益偏差,而不得不使农村人加大流动寻利的力度。
设想有朝一日农村也有了这种立法权和行政权,他们反过头来对城市进行种种的立法设限,如对城市与农村实行二元化管理,将粮食禁运,菜品禁运,资源禁运,禁止城市人出城,或是必须办理“出城证”或“进村证”,取消一切现有特权和福利并归之于农村等等,这样完全脱离了农村供养的城市就会成为人肉孤岛,城市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还会存在吗?
这种假设并不遥远,就在60多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就是以此法来围困长春守敌的,并且还让那些流民全部涌入城内,尽食其粟,直至粮绝人尽而破城。
渭泾分明,壁垒禁严,尊卑有致,这是城市以仇恨的心态设计的社会制度,虽然名义上占据着道德的高地,但并不占有实质的真理和道义,自然没有权力来诅咒农村人反弹和抗争,更不能以二次立法的形式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并再以法律的名义来打压农村的过激行为,这实在是变本加历的精神变态了。
学会感恩,不但是弱势对强势“恩赐”行为的表示,更是强势反思自己之所以能够强势的原因的过程,想想谁才是自己真正的衣食父母,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要成为“卧槽泥马勒戈壁”般占着茅坑不拉屎,更不要让这种仇恨心理一旦成为颠覆中国社会的又一根导火索,到时还要骂农民不懂现代政治,崇尚暴力才好。
学会感恩,就是要用强制性的法律来改变现有的“城尊村卑”的现实,从根本上给予城乡同等的政治待遇,让这种二元割裂的社会自动吻合,避免城乡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一切不稳定因素的首要之险。
看来,不但在食物上要尊循自然与绿色,在政治权力和制度设计上,同样也不可有违自然的规律,也要尊循自然与和谐,方可保社会生活一切井然而有序。
2009.3.11.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