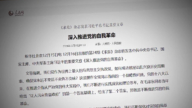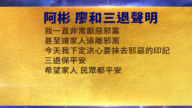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7月20日訊】觀衆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禁聞特別報導。
24年前的今天,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針對修煉人群體進行滅絕性迫害。在這場長達24年的迫害中,無數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判刑,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但是,殘酷的迫害,始終無法動搖這群修煉者對「真、善、忍」的堅定信仰。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來看潘奇和田耘海的故事。
熱氣騰騰的7月天,滾燙的柏油路,行人快速的穿梭,潘奇和田耘海兩個人像往常一樣,搭地鐵再轉公車,一起上班、一起回家。這種平凡的日常對他們來說,是得之不易的珍貴。
1996年的春天,還在大連醫科大學就讀的潘奇,青春洋溢。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修煉法輪功。2005年3月拿到執業醫生執業證書,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認識了田耘海。
前大連某診所主治醫生潘奇:「因為1999年『7·20』,中共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後,我因為是修煉法輪功的,我就覺得那個電視上所講的都不是真實的情況。我們當時的時候有一念,就是說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澄清。他在那裡租了一個房子,裡邊有(法輪功真相)資料。」
前中共鐵道部十三局助理經濟師田耘海:「潘奇每次就是來幫幫忙,印印資料,完了之後呢,負責把她所認識的同修,那一片的同修的資料,她每週就給運出去。因為她身材很小,她每天要背一個大包,很重的大包,要把週五的資料運到,再挨家挨戶的分出去。所以有時候我看到很重,我又有一些時間,我就幫幫她運資料。」
田耘海是東北吉林人,大學畢業後,在大連工作,受到上司的重視。然而中共迫害法輪功後,田耘海經常到北京上訪,由於擔心中共的株連政策會牽連單位領導,他主動辭職,也退了黨。此後他留在大連,繼續揭露中共造謠迫害法輪功的事實。
田耘海:「共產黨造了很多的謊言,尤其是天門自焚這件事情,對人的那個影響非常大,我們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沒人知道這件事情,那麼怎麼辦?那麼大家就印一些資料(去分發)。」
隨後,潘奇和田耘海被非法關押。潘奇的家人通過各種管道,把潘奇營救出去,田耘海則繼續被關押。
潘奇:「那年2005年7月吧,那一天就是週五,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去拿資料,就是一開門幾個國保就一下子把我就拽進去了,力度非常大非常快,就是當時我想喊都沒有喊得出來,然後我就知道出事了。」
潘奇:「他在法輪功被迫害的時候,就是非常勇敢的承擔了起來,在當地幫助我們做資料這個事情,他沒有工作,他是主要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的。我就覺得對他就更擔心,因為我知道這個迫害非常邪惡,因為我也五六次被關押。」
2006年4月17日,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中共非法開庭對田耘海羅織罪名,以所謂的「破壞法律實施罪」重判10年刑期。
田耘海從大連看守所,轉到瓦房店監獄,然後轉到盤錦監獄。
潘奇:「因為當時有人說,有活摘器官的事情,而且尤其針對那些就沒有家屬關照的人,他們就會失蹤,他們的器官就會被移植。當時我就想,我應該馬上通知他的家屬,讓他們去跟蹤這件事情。」
田耘海:「從看守所開始,一直到入監監獄,一直到監獄和輾轉不同的監獄,每一次、每年我都要進行血檢,就是這個血液的檢驗。當時也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反正就是表面上說為你的健康著想,每次都要體檢,抽一管血。」
田耘海在被剝奪自由期間,多次遭到警方酷刑。
田耘海:「可以說大家平常所知道的酷刑,我都經歷過,所以一言難盡。可能大家看過電影或者是電視劇裡邊有那個人,把人捆起來,他用一種布條,他把我全身纏住,把我的手腳,就是全身固定在床上,就是我一動都動不了,甚至我的頭都無法動,那在三天三夜的過程中,身體已經沒有知覺了。」
田耘海:「我親眼看到一個法輪功的學員,被電過之後無法飲食,之後,眼睜睜地看他在這死去,沒有辦法。就是我們在那種環境,就是人在一個完全封閉的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人沒有任何,你可以去向人表達和尋求保護的情況下,你只能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默默地發生,你沒有任何辦法。」
正在潘奇想著應該如何幫助田耘海時,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田耘海被電擊,生命垂危。潘奇趕緊連絡田耘海父母,一起趕到盤錦監獄。
田耘海:「我告訴家人,我說我不會自殺的,如果我要死在這裡,一定是他們迫害死的,他們電我了,他們把我銬在鐵凳子上,折磨我,他們馬上就把我帶回監獄,不讓我說了。那是我見到潘奇的第二面。之後我絕食了一段時間了,絕食了將近五個多月的時間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犯人曾經跟我說,他說外邊有個人喊你的名字,是個女的,後來我知道,那是潘奇。」
當時的潘奇,下定決心把田耘海救出來,儘管當時中共高壓監控,但這些都不足以撼動她。
潘奇:「我其實都記不得去多少次了,因為我有這個條件,只要我能去的我都在去。我能盡量找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住下來,第二天早上就去田耘海的監區,然後就是在外面站著,或者是找他的隊長。」
田耘海:「那個時候是千金難買的,是無以回報的,因為在最艱難的情況,而且她面臨的迫害,大家不敢接觸那些邪惡的機關,一接觸的話,都會有失去自由危險的情況,所以她能去做這個事情,當時應該說是在我生命當中最值得珍貴的記憶。我覺得一個陌生的人,一個沒有跟我任何關係的人,在那個情況下她知道我最需要什麼,所以那個時候就給我留下永久的記憶了。」
潘奇:「當然我會有危險,那麼這時候最好的情況就是我離開當地,可能就是尋找一個地方,那我可能就是安全的。但是我想同修還在監獄裡邊,我想我第一做到的事情是把這些事情曝光,讓所有人知道。」
田耘海:「這個邪黨它非常邪惡的地方,就是防止把封閉監獄這種消息傳遞出去,外人不讓接見,尤其是你是煉法輪功的,你讓法輪功來接見你,那絕對不可以的,所以他們就斷絕消息來源。所以潘奇想見我是見不到的,後來我聽說她是以未婚妻的方式,才可以見到我。」
潘奇:「那個時候就是說我是田耘海的朋友,我去看他,他說朋友那不行,我說我是他的未婚妻,然後他們就說,這個未婚妻有證據嗎?我說那你等等,我回去辦手續,然後就把那些所有的手續,就是我這部分全都辦好了,我說,我是要跟田耘海結婚的。我那邊的手續已經辦好了,就等著你這邊的手續了。」
潘奇鼓勵田耘海要堅持信仰、要保護好自己,要活著出去。然而潘奇不知道,自己被當地警察盯上了。當她再次去盤錦監獄時,被一群警察攔住去路並粗暴亂翻她的隨身行李,不讓她去監獄看田耘海。
潘奇:「本來要抓我那個,他應該是個副所長,他帶了一群人,這個時候他們就在一起商議。然後那個副所長看了一下就說,意思就是說我是大連醫科大學畢業的,我姐姐當時是高中的教師,那我弟弟是大連的海關,他就說我們都是一些高學歷的人,我們不應該待在監獄裡面,他就幫了我一把,他說那你就快點走,就是不要再來了。」
大連當地派出所的警察正商量著要再次抓她。潘奇擔心家人也遭到打壓,於是帶著牽掛和不捨她離開了中國。
後來田耘海再被轉到瀋陽監獄,獄方加劇了迫害,從2014年4月開始,拒絕家人探視。
田耘海:「這個時候感覺我就要放棄了,我不僅要放棄我的生命,我放棄我的信仰,真的有這種感受,就是我已經無法承受了,那麼怎麼辦?我在那一瞬間,有兩個犯人在那對話,傳到我的耳裡,兩個犯人是這麼說的,『我看他挺不過今天晚上了』,我當時意識還清楚,能夠聽到他們在對話。『他挺不過今天晚上了』『那還有什麼辦法呢?』『他這不鬆口,那還有什麼辦法呢?』有一個人用電話搖電,來電我。這時候我非常恐懼,我的意識還有,就是我非常疲勞,很痛苦,但是我意識還有,因為我痛苦已經到我頭都抬不起來了,我就坐在椅子上,我頭都抬不起來的狀態下,他們說你看這還是修煉人,他們就傳到我耳裡這麼一句話,『你還是修煉人』,我這腦裡靈光一顯,就顯出一個念頭,喔,我還是修煉人,那麼死也堂堂正正的死,我就狠狠的硬把頭挺起來了。」
2015年,田耘海終於被釋放出來了,但也面臨著隨時被抓回去的風險。此時在美國的潘奇,也在思考如何營救田耘海脫離魔掌,她想也許可以以夫妻的名義申請田耘海來美國。
潘奇:「我經常我就會夢到,大概是田耘海他倒的時候我都在扶他,扶他一下,再扶他一下,再扶他一下,我覺得這個路是我要走的路。」
田耘海:「我的家人一直跟我受著痛苦和煎熬,擔心受怕,所以我在監獄裡就有一個打算,有個願望,我想我這次出獄,好好孝敬你們,我不離開你們,我在你們身邊,我工作生活就這樣。媽媽說,哎呀海呀,就是你別那麼想,你要安定了,我們就是最高興的,就最放心了。」
在父母的鼓勵下,田耘海和潘奇開始計劃這次「婚禮」。
田耘海:「因為潘奇是回不了大陸,她被列黑名單了,就是我們想結婚,她也回不了大陸,後來偶爾從網上得知消息,就是香港的法院結婚證,是海牙法院認證的,也就是國際同認的,那麼說,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到香港結婚。」
潘奇:「我們在香港的時候,我們拍了很多照片,但我們拍的時候其實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不像別人那樣。我們結婚的時候周圍也沒有人,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我們拍照片的時候心情也是不一樣,有的時候是為了申請,還心裡沉甸甸的想著我們是否能成功。」
這場「婚禮」沒有新人的喜悅,也沒有所謂的浪漫愛情故事,更多的是驚險和痛苦。
田耘海:「在(赴美)簽證過程中也是,也不那麼順利,可是最後我把那個,我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拘留證和法院的判刑書,檢察院的起訴書,我給那個簽證官看了之後,他給我特赦,開了特赦通道。」
潘奇:「所有的手續都辦完了,進入海關了,他就已經啟程了。我那個時候我就聽到一個聲音,來了來了,我就覺得是沒有問題。當時的時候我就發了一念『師父謝謝你,就是我把您的弟子也帶來了』。」
黑暗過去,迎來的是黎明的朝陽。2023年7月的紐約,陽光灑滿整個街道。在田耘海身邊,潘奇一路默默的跟著。難以想像一個弱小的身軀竟然能走過如此的苦難,那股堅強的意志力是美麗的音符,譜出的生命樂章讓聞者為之動容。
新唐人電視中國禁聞組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