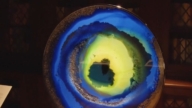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1日訊】
第三章 君體第一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躬,傾己勤勞,以行德義,此乃君之體也。
隋唐家訓發達,社會流傳「養男不教,為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豬。」(敦煌文書《太公家教》)不僅出了被稱為「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7卷20篇,中國仕宦家訓的集大成者),也湧現了帝王家訓的高峰——《帝範》。
太宗好學,素養很深,頗多獨到之見,可《帝範》並非一部理論著作,而是太宗治國平天下經驗之昇華。讀《帝範》,尤須著眼於其實踐性的特點。
太宗之被稱為千古一帝,其超邁之處自謂有三:「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貞觀政要‧慎終》)

太宗怎麼做到的呢?《帝範》十二篇就是答案。而《帝範》的第一篇,就是「君體」。何謂君體?
人君,內聖外王,才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濟民者,生之、養之、教之。「教」就是「教化」,這是人君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標準。人君憑什麼來教化呢?修己。修到什麼程度呢?「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具體而言,太宗講了四條:寬大,平正,威德,慈厚,下面分別討論之。
第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太宗躬行王道,直追兩王三代之政(兩王指堯、舜,三代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其胸襟無與倫比,首先強調「寬大」,即以寬為體(而非寬猛並列,猛僅是調劑手段),這就超越了前賢所謂的「寬猛相濟」論。
太宗倡導「寬大」,既是對古人相關思想的發揚光大(如《虞夏書•大禹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是躬行王道的具體表現。
舉例而言,在唐朝以前,死刑案件只需「三復奏」,從太宗開始,擴展到五次,為什麼?太宗對大臣強調:「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又如,在法律上如何對待「疑罪」?太宗朝,在「德本刑用」理念指導下制定的唐律頗寬仁,明文規定「疑罪從輕」、「疑罪從贖」。後人評論:唐律「終之以疑獄,其所以矜恤罪囚而惟恐稍有錯失者,可謂無微不至矣」,而元、明、清法律「刪去疑獄一條,均失唐律之意」。又如,貞觀六年冬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以一個月為期,處理好後事之後再自動回來受刑;居然,死囚一個都不少回到了監獄。
正是因為太宗志存高遠,治國以道,所以只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古昔未有的繁榮景象。
第二,「平正,其心足以制斷」。決斷力是人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猶豫不決、錯過時機最是大忌。當機立斷的決斷力從何而來?來自心之「平正」。人君很難不受身邊人、外在環境的影響;內心的七情六慾,又容易使人瞻前顧後,捨不得這個又流連那個。人君修身修什麼?就是修這顆心,使心一做到「平」,二做到「正」。怎麼做到呢?《大學》講得非常清楚了(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貞觀政要》記載了太宗一段議論,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何謂「寬大」、「平正」。隋文帝大事小事都要親自過問,太宗卻放手宰相、群臣處理政務,兩者對比為什麼會如此鮮明呢?是因為前者「心暗」,後者坦蕩。(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第三,「非威德無以致遠」。人君要四海歸心,靠什麼?威德。威德怎麼來?立功。功績卓著,天下懾服。無尺寸之功,人家怎麼會服氣你呢?人君雖可靠世襲掌權柄,但這只解決了權力來源問題;要人心悅誠服,還得靠政績說話,這也是能力的體現。否則,庸庸弱弱,很可能大權旁落,甚至受制於權臣、外戚、家奴(宦官)。
但是,僅「立功」是遠遠不夠的。例如,隋煬帝修大運河,溝通南北,功在千秋,卻導致民怨沸騰。為什麼?晚唐詩人皮日休說:「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是批評煬帝的動機、品行。歷代為什麼稱頌大禹呢?因為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夏本紀》),威德赫赫。《論語》記載孔子論大禹:自己吃得很差,祭祀鬼神時卻很豐盛;自己穿得很差,祭祀的衣服和帽子卻做得非常華美;自己住得很差,農田水利卻治理得很好。(子曰:「禹,吾無間然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也。」)
因此,「立功」對人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德」。只有用心純正、心懷天下、修身進德,做的事才有威德,讓人心悅誠服。《韓非子•五蠹》記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所以,孔子講:「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
太宗「華夷一家」,風行萬里,被各族尊稱為「天可汗」,開古今未有之盛況,是「非威德無以致遠」的光輝典範。

第四,非慈厚無以懷人。中國傳統文化歷來講家國一體。人君如父,臣民如子。皇帝之所以以「祖」、「宗」為稱,官員之被稱為「父母官」,就是講天下都是一家人。父慈子孝,人君就要以慈厚為懷。《貞觀政要》記載了太宗如下一段話: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雖然隋文帝是否「惜倉儲不憐百姓」或有爭論,但人君須以慈厚懷人,則是太宗極為強調的。
以上「寬大、平正、威德、慈厚」四條,是人君修身的方向。怎麼著手呢?太宗也講了四條:奉先思孝,處位思躬,傾己勤勞,以行德義。也就是說,孝順祖先(中國近兩千多年,歷朝都講「本朝以孝治天下」),居位恭敬,勤政愛民,躬行德義。
太宗這麼教導太子,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春秋以降,王道講了千百年,也多帝王推崇,但實現的不多,那麼仁政思想是不是空想呢,懸得太高?貞觀之治的出現,證明了王道是可行的,關鍵在於人君。貞觀之治,也深刻影響著其後的中國歷史。太宗《帝範》十二篇以「君體」為第一,為文最短但最為精要,其意深矣。
最後,我們再簡單講一下《帝範》十二篇的邏輯結構等諸問題。
首先,《帝範》為什麼是十二篇?「十二」這個數字有什麼講究?古代人為了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情況和氣節的變換情況,把周天分為十二的等分,叫做十二次,故「十二」是古來所謂法天之數。《左傳•哀公七年》:「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當初,舜定天下為十二州,就是法天。
其次,《帝範》十二篇之間是什麼關係?這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帝範》四庫本將十二篇分為四卷,筆者認為較為合理。
卷一主線是講為國立本,包括君體、建親、求賢三篇。國家安危繫於人君一身,故君體為第一。人君以修身為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中庸》)故建親為第二,求賢為第三。
卷二主線是講人君如何保持聖明,包括審官、納諫、去讒三篇。治理國家須藉助於官,而官是否得其人呢?故審官為第四。人君居於深宮,如何保持耳聰目明?廣開言路是也。故納諫為第五。人君亦有七情六慾,小人往往籍此而進讒言,禍害極深,此國之大賊,故去讒為第六。
卷三主線是講正風氣,包括誡盈、崇儉、賞罰三篇。大凡盈則滿,滿則奢,滿則驕;人君盈往往傾邦危城。故誡盈為第七。那又怎麼誡盈呢?去奢從約。故崇儉為第八。賞罰為人君之利器,運用是否得當關係一國之風氣,不可不慎,故賞罰為第九。
卷四主線是講國策,包括務農、閱武、崇文三篇。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人君當以農立國、足食為政。故務農為第十。文事、武備是為政之兩翼,「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孔子家語•相魯》)「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故閱武為第十一。而要宏廣風化,導引習俗,懷柔天下,則必崇文厚德。故崇文為第十二,壓軸之篇。
綜上所述,《帝範》全書結構嚴謹,每篇自成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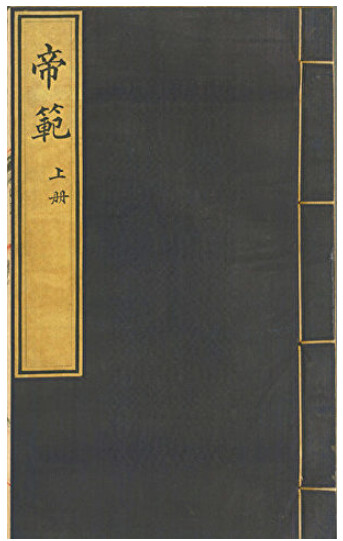
再次,《帝範》十二篇與儒家經典《中庸》「治國九經」是什麼關係?《中庸》講:「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太宗深研儒學,對《中庸》「治國九經」自然熟悉;那麼,太宗為什麼沒沿用「治國九經」的框架呢?這是因為,其一,歷史時代不同了(《中庸》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著者雖嚮往西周制度,但其已在瓦解中了;至唐,郡縣制已經定型);其二,太宗是個實際操作者,雖繼承了《中庸》的精神實質,但對「治國九經」不能不有所損益。但是,《帝範》十二篇與《中庸》「治國九經」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第四,《帝範》、《貞觀政要》與貞觀之治的關係。除了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外,《貞觀政要》是後人了解貞觀之治的最重要材料了。史官吳兢(670—749),史稱「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吳兢利用業餘時間編撰《貞觀政要》,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脫胎於《帝範》。兩者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範》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因此,《帝範》乃是貞觀之治的綱領與精髓。
附錄:「君體第一」大意
人民,是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國家,是君王統治天下的根本。國君為政之本,精微高大,如同山嶽,高聳雲霄而巍然不動;如同日月,普照大地而光輝燦爛。億萬百姓為之瞻仰,天下為之歸心。君王治國,寬大,心胸坦蕩包容萬物;平正,心智明辨而又決斷。君王沒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遠方四夷之人歸附;君王沒有仁慈的胸懷和寬厚的品質,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因此,要以仁義去撫育皇室宗族,以禮儀去尊重大臣。舉行宗廟祭祀,侍奉祖先,要時時將孝道掛在心中;身處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態度待人;將全部身心傾注於勤勞國事,推行德義,這就是為君之體。@*#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