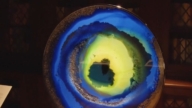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9月11日訊】燦爛輝煌的文藝復興可謂是西方藝術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了,其影響之深遠,猶如歷史篇章裡的黃鐘大呂,震古爍今。本次人類文明中的美術在文藝復興時期走向成熟,並對其後兩百年的西方藝術有著直接的影響。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之後的兩百年卻是各類相生相剋因素處於激烈而又微妙的衝突下,陰陽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階段,所涉及因素之龐雜、其背後範圍之深遠,絕非筆者一兩篇文章所能講得清楚的。因此,本文只是根據個人粗淺的理解,從幾個方面簡單地談一談當時西方美術的大致情況,以及這段歷史帶給人的一些啟示。
相對與相合
在美術創作題材方面,天主教與新教的態度截然相反,這與歷史有關。自文明伊始,人類就不斷通過美術作品去表現對神的崇敬和對天國的嚮往。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占據主導思想時,教會就利用美術作品向大量不識字的人宣講教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一直鼓勵藝術家表現神聖題材。
不僅如此,美術作品還在一些通過祈禱和默想來修行的基督教宗派裡扮演著幫助修士進入修煉狀態的角色,(詳情請見《從一段藝術史看人類思想的變遷》:
例如十二世紀,天主教的熙篤會(Cistercians)發現在禱告時,偏黑白類單色可以幫助修士消除雜念,因此開始要求一些教堂和修道院把彩色玻璃花窗做成單色的,以減少感官刺激,讓人更加專注於修行。
這種做法逐漸蔓延到其他修會,以至於在一定範圍內形成習俗。從十三世紀中期開始,淺灰色的花窗在一些地區便成為了時尚;而到了十五世紀,北方已能時常看到一種流行的做法:一些宗派的修士們會在每年四十天的大齋期間將樸素無色的布匹鋪在彩色祭壇上遮擋;如果祭壇畫是三聯的,便無需外物遮擋,因為三聯畫的左右兩邊可像兩扇門一樣關上,遮住中間彩色的主畫,而在關閉的那一面則會要求畫家繪製兩幅單色的圖,其灰色在專業上被稱作「Grisaille」。

宗教改革與新教出現後,信仰的波動影響到了方方面面,也包括美術。不同於文藝復興盛期各類藝術思想、技法風格層出不窮的拓展狀態,藝術的發展在相生相剋的因素中越來越體現出不同陣營各自收緊與統合的趨勢。而當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尋求收緊時,不同因素的對立就體現得越來越明顯。
我們看到,印刷術的普及促進了書籍出版與文化發展,可是宗教機構的圖書檢查制度又銷毀了大量書籍;天主教願意把一切傳統藝術元素都納入教堂,而新教以反對偶像崇拜為由把教堂裡的美術因素削減到最少;宗教力量加緊打壓反宗教勢力,但崇尚科學研究的反抗勢力卻日益強盛;在宗教內部,天主教以異端為名處死了不少新教教徒,而新教統治區也以火刑對天主教徒還以顏色……
在這複雜的時代背景下,特倫托會議(Council of Trent,1545年 – 1563年)後,針對藝術界在文藝復興時期所出現的濫用宗教主題的亂象,天主教會決定對宗教圖像的形式與內容進行嚴格規範,要求藝術家描繪宗教主題時應呈現莊嚴的場景,並在作品中表達出神聖的感情。
隨著十六世紀下半葉宗教戰爭的白熱化,天主教與新教在對美術的態度上也向兩極化發展。新教反對天主教會的腐敗與奢華,因此在藝術上主張簡樸,並且嚴禁各類可能涉及偶像崇拜的主題。而新教所反對的,卻正好是天主教所支持的,因為天主教並不認為千年來藝術界描繪神的一貫傳統就是偶像崇拜。在這方面早有經驗的羅馬教廷便把資金投入到有才華的藝術家那裡,讓他們以無比燦爛的視覺藝術來描繪天堂的壯麗,把天主教的大教堂裝飾成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殿堂,藉此吸引大眾皈依。
由於和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強調靜謐、均衡的風格區別較大,令人耳目一新,從十六世紀末開始,這種氣勢宏大、富於動感的藝術便從羅馬、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迅速遍及歐洲,後人稱它為「巴洛克」(Baroque)。很快,整個藝術領域,包括繪畫、音樂、建築、裝飾藝術等各方面都開始充滿了運動、變化與恢宏氣勢,這種趨勢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進入全盛時期。

同時與巴洛克相對應的,還有一種主要的藝術風格,就是繼承文藝復興美學觀的古典主義(Classicism)風格。這種藝術品味原本就一直存在,尤其在法國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路易十四(Louis XIV)時期得到了王室的扶持。古典主義美術以古希臘、古羅馬藝術為典範,崇尚理性,遵循規範,在典雅、和諧的藝術中尋求真理。
同十七世紀歐洲各國的君主一樣,法國的統治者們在國力上升時期也希望藉助藝術的宣傳力量,來彰顯他們的權威。以天主教為國教的法蘭西在美術上沒有新教國家的那些禁忌,同時法國從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開始就早已形成了發展藝術的國家傳統,因此法國王室不斷投入資金,依靠藝術的感染力來鞏固人們頭腦中「君權神授」的思想。

正如法國在美術上所承載的文化使命那樣,1648年,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的建立奠定了此後三個世紀法國在西方美術界的領先地位。法國的美術學院並非史上最早的美院,但卻是在強盛的國力與合適的時機下建立起來的,讓西方藝術的中心逐漸從意大利轉向了法國。藝術學院制度的推廣其實也是走回了西方史前文明中藝術的學術化承傳之路。法國美院在發展過程中非常注重學術研究,提出的藝術理論日趨成熟,因此受到各國的重視。
當時作為另一個藝術繁榮地區的荷蘭雖然美術經濟發達,但在當地盛行一時的風俗畫終究顯得不夠高雅,缺乏深度,很快便如潮水般消退。非常依賴市場經濟的荷蘭美術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沒有形成牢固的學術體系,缺乏有影響力的美術理論專著,造成美術上的學術性不足。藝術終究是一門精神性很強的學科,光靠經濟基礎還是不夠的。
南邊的佛蘭德斯等地原本與荷蘭都屬於尼德蘭,從1556年開始被西班牙統治。1581年,北部七省獨立為荷蘭共和國後,南部剩下的地區仍然由信天主教的西班牙統治。因此在十七世紀,兩邊藝術的發展便分道揚鑣。不同於荷蘭畫家,不論是來自安特衛普的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還是來自布魯塞爾的尚拜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1629年轉籍法國),他們作畫時完全無需考慮新教禁令,只管全身心地用高超的技藝在作品中表達對神的崇敬。事實證明,藝術只有表現神才會興盛,而神也會賜福於作畫之人。這些畫家無論在當世或後世都享譽盛名,衣食無憂。這與荷蘭畫家們通過降價營銷追求市場競爭力,以致於大批藝術家最終貧困潦倒的悲慘境遇完全是天壤之別。
美術學院的建立也體現出此時藝術的收緊與規範。這種由教師統一授課、學生集體學習的方式自然不同於以前藝術圈內作坊式的學徒制,也引起了整體藝術風格的規則化。原來分散於各地的小流派在這種大一統的趨勢下逐漸減少,不同國家的繪畫風格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也慢慢呈現出一定的統合趨勢。
由於學院的規範化特點,富於個人激情類的作品是不被鼓勵的,所以學院派整體上偏向於古典主義美術風格,強調造型、平衡、素描關係等因素,而不鼓勵學生著手大量色彩學派的研究。但看重色彩、明暗、動勢、激情的巴洛克藝術家們則想方設法把他們的藝術理念引入學院之內。因此,與其說古典主義風格與巴洛克潮流對抗,不如說這兩者是一種競爭與共生的關係。尤其是十七世紀末以後,越來越多的巴洛克藝術家在學院高層任職,也讓學院藝術風格處於變化之中。
這種相生相剋的關係讓巴洛克與古典主義一動一靜,相得益彰,在很多地方都能體現出來。比如著名的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就是巴洛克與古典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凡爾賽宮的宮殿是古典主義風格建築,但其內部裝潢則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數廳堂是巴洛克的變體洛可可(Rococo)風格。可見,當時人們的審美並不會被單一的藝術流派所禁錮。
(待續)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