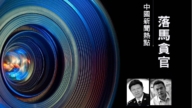2017年3月6日,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在北京開會。美聯社當時說,孫政才是爭取在中共十九大成為政治局常委的競爭者之一。
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孫政才落馬了。世界對孫的瞭解與興趣,遠低於他的前任薄熙來,人們說得最多的是重慶魔咒。雖然媒體談到他的腐敗,例如因名表多而得「表叔」之綽號、他妻子是民生銀行夫人俱樂部成員、他兒子讀康奈爾大學的每年7萬美元學費問題,但幾乎大多數媒體都明白,他是原先的「接班人」之一,禍起「山頭主義」才是真正的原因。
東宮之變,兩年前就有預兆
孫政才與胡春華二人在中共十八大上被選入政治局,一直被視為習李十年後的接班梯隊。如果中共從江胡以來形成的「接班人梯隊」制度不變,那麼,作為這屆政治局僅有的兩位「60後」之一,在即將到來的十九大上,二人原本有可能憑藉地位和年齡優勢,被安排再高升一步,成為二十大的「接班梯隊」成員之一。
但是,世事多變。2015年8月10日,大陸官媒發布消息《正廳級團干「降格」使用釋放什麼信號?》,文中直言共青團幹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層歷練。更重要的是,文章點了被認為是「團派」干將的胡春華、周強、陸昊等多位黨政大員的「名諱」,並舉出浙江團省委書記周艷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層用人的新方向,而「團組織和團幹部的面貌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轉變」。
自那以後,誰都知道胡春華東宮之位無望,如今又輪到了另一位接班人孫政才出局,這就帶出了一個大陸官場人人在想、人人都不敢說出來的問題:究竟是「接班梯隊」需要更新,還是「接班人制度」生變?但不管屬於哪一種情況,其實都與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權力交接有關。西方國家眾多研究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但前蘇聯、中國、北韓等共產黨國家在接班人問題的經驗很不相同,未能總結出規律。本文僅就中共的「接班人」問題,進行梳理探討。
紅色專制政權的「接班人」選定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紅色專制政權在俄國誕生以來,共產黨政權最高領導人的更替從來只有兩種:一是死前指定;二是最高領導人死後,高層經過一番鬥爭,最後,或者臣服於一人,或者由一個領導群體共同執政。如果是高層臣服於一人,便成為個人集權領導模式;如果是領導群體共同執政,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模式。
蘇共執政時期,從未出現過最高領導人生前指定接班人的情況。列寧死前對斯大林不滿意,但蘇共的最高權力最後落入斯大林之手;斯大林死後,雖然最高領導人迭次更替,但歷任最高領導人一直未形成真正的個人集權領導模式,因此,蘇共長期處於集體領導模式狀態。
而中共領導人則對「接班人」問題頗多琢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之後,舉國飢饉,餓死幾千萬農民,他為了逃避個人責任,把爛攤子甩給劉少奇去收拾,自己「退居」二線。1961年9月24日毛在武漢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首次告訴外國訪客,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但那是毛的「煙幕彈」,實際上毛那時已經在暗中尋找打倒劉少奇的機會,發動「文革」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接著,毛澤東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兩年之後林彪死於非命。毛澤東死後,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地位脆弱,很快就被迫辭職,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一批中共元老開始集體執政。「六四」之前,江澤民被指定接班,但江就任後隨著陳雲系保守派大佬的步調起舞,于是有了鄧的南巡,宣稱「誰不改革誰下臺」,江這個接班人一度也風雨飄搖。
中共的「接班人」梯隊制度化
鄧小平晚年,中共為了政權的穩定,創立了共產黨國家的首個「接班人」梯隊制度化。這是指以十年到二十年為期,建立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梯隊」,限定現任最高層成員的任期,對「候補梯隊」成員刻意栽培,屆滿換人。胡錦濤被隔代指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便是這個「接班人」梯隊制度化的結果;而胡錦濤在第二個任期依樣畫葫蘆,又建立了新的「接班人梯隊」,胡春華和孫政才就是主要成員。
本來,「紅二代」才是鄧時代高層最中意的「接班人梯隊」,但多數「紅二代」在「文革」時期依靠父輩權勢關係,躲進部隊裡,逃避上山下鄉,結果恢復高考時反而因任職軍中而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因此,他們當中,具有大學學歷的人為數不多,而在地方上基層任職歷練過程中得以順利陞遷的,更是屈指可數。在有限的幾個參加政治「馬拉松長跑」的「選手」當中,陳雲之子陳元「起跑」最快,其次是劉少奇之子劉源,可這兩人都因官場風評不佳而不得不中途退賽,剩下習近平和薄熙來兩位選手繼續參賽,習近平成功到達「終點」。如今,絕大多數「紅二代」已年近古稀,當年既未進入「接班人梯隊」,現在當然只能到齡退休。
接班人梯隊」中「紅二代」的缺席,給團幹部讓出了「天賜良機」。由於胡耀邦任總書記的年代開始強調幹部的年青化、知識化,當時符合這個條件的,許多人是原共青團幹部,于是團系統的幹部成為各級官員的「接班人梯隊」這一未成文規則,也自然而然地延續下來。直到2015年8月,團幹部這一「欽賜」地位才被動搖。
個人集權和集體領導的「鐘擺式」來回擺動
2016年2月2日,程曉農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寧馨的專訪,在這篇題為「習近平導引中國,旗指何方」的專訪中,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論,即共產黨領導模式的「鐘擺論」,指出這類政權的領導模式通常都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意的。一般來說,第一階段,共產黨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黨內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必然成為常態,最後個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領導人如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就取代了集體領導,進入領導模式的第二階段。個人威權的領導人去世後,就進入第三階段,重回集體領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華國鋒、鄧小平到胡錦濤,基本上都是如此。蘇聯在第三階段的末尾解體了,而中國現在進入了第四階段,即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
程曉農認為,領導模式的選擇與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時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于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斯大林和毛澤東死後,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同時給老百姓一些實惠,建立權力後繼者的合法性,赫魯曉夫和鄧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過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敗就死灰復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則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用腐敗換政治穩定,會大量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這種局面能否長期維持下去,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條件;當局的經濟資源快要耗盡時,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蘇聯,或者是「擰緊螺絲」、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轉向個人集權領導模式。
未改極權性質,鐘擺兩端難論短長
目前,國內一些不滿專制的知識份子對中共新的個人集權領導模式非常不滿,視之為倒退,彷彿「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模式離民主化更近一些。這裡必須廓清兩個問題:
一、個人集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都是共產黨政權領導體制這塊「硬幣」的兩面,非此即彼,無論哪一種,都與民主化毫無關係,不過是極權國家領導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對習近平集權想建立獨裁的批評,那是假定集體領導不是獨裁,個人專斷才是獨裁。對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從一戰以來,世界的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世紀60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機》1、2,VOA,2016年5月17-18日)。
二、從制度層面看,不管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在集體領導和個人集權之間怎樣來回擺動,其專制的制度層面並沒有根本性變化;如果說有差別的話,主要體現為政策鬆緊、政治高壓大小。雖然在集體領導模式下,很多時候會實行相對寬鬆的政策,這正是國內知識份子反感個人集權模式的原因,但是,集體領導模式並不必然保持寬鬆政策,一切視當局維繫政權的需要而定。「六四」鎮壓就是最好的例子,鎮壓前後中共的集體領導模式並未發生重大轉變,但鎮壓之後的政治高壓至今令許多過來人記憶猶新。集體領導模式下之所以會實行寬鬆政策,其實主要是統治者需要挽回民心,懷柔而已。一旦民眾奮起呼籲民主時,集體領導模式的紅色政權會毫不猶豫地殘酷鎮壓;甚至僅僅是因為民間團體的規模過大,比如法輪功、基督教家庭教會等,其實並無民主政治訴求,也同樣會遭到殘酷鎮壓。
過去幾年,國內經常用「九龍治水」來形容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這種高層的權力分散,是腐敗升級到最高階段的政治保障。現在,中國的經濟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機隱約可見,統治者為了保住政權,減少內部紛爭,轉向集權,以便對官員「擰緊螺絲」、堵住「外逃」之路。這與當年鄧、江、胡時代實施懷柔政策的目的其實差不多,都是從延續政權壽命出發的。而官員的腐敗有如白蟻,正在腐蝕政權的支柱之時,政權保衛戰成為當局的首要任務,習近平視自己為保護紅色政權的不二人選,實行多年的「接班人」梯隊制度化自然就「退居二線」了。
──轉自《阿波羅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