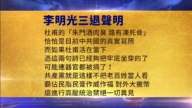(接上文)
十六
1997年7月2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那年7月1日中國收回對香港的主權,全國破例放一天假,2號才上班。一上班,一位同事就把一套書往我桌上一放,說:「給,《轉法輪》!」
我一看,是大妹妹從綿陽寄來的包裹,包裝已經破損,所以同事看見了書名。我從小就愛看書,大學和研究生時代,哲學、宗教、人體特異功能、氣功、《周易》等等,幾乎甚麼都研究過。一方面,我總相信宇宙能維持穩定和和諧,一定存在著某個終極真理,我想知道那個真理到底是甚麼;另一方面,我對人有了這條命到底應該拿來幹甚麼,感到相當困惑。人難道就是應該為了活著而活著,追逐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然後一死了之嗎?
許多時候,我找不著北。我不願像周圍許多人那樣爭爭鬥鬥、溜須拍馬,削尖腦袋往上爬,我覺得那樣太累了,太有悖我的本性了。可我又不甘心由於我的不「奮鬥」而落於人後,被人欺負,讓人瞧不起。我不知應該遵從和堅守甚麼,許多時候很迷茫、很困惑。表面的成功和風光那是給別人看的,一點兒也解不了我心中的惑。
再加之,92年我分娩時因醫療事故造成大出血,又因輸血染上醫學上尚無藥可治的丙型肝炎,從此人生陷入低谷和絕望中,在醫院裡一躺就是好多年。
97年初,雖然在經歷了好幾年的住院「生涯」後勉強開始上班,但也只是因為我不願一輩子當疾病的奴隸。我因醫療事故而倒下時,才剛剛工作了一年多。人們常將女性比作鮮花,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朵還未來得及完全綻放的鮮花,卻在疾病的摧殘下一夜凋零。我不甘心讓人生就此葬送在醫院,想「假裝」自己還正常,不管還剩多少時間,我都想讓自己「正常」的活著。
話是這樣說,可我自己知道,我活得比《紅樓夢》裡的林妹妹還累,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做錯一件事,唯恐被疾病恥笑了去。我的身體實在太弱,一有點兒風吹草動、流行感冒之類的,我第一個就倒下。
因此,到97年7月,在經歷那麼多之後,我是以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情打開《轉法輪》的。可是,當我讀到第四頁中關於人的生命來源的闡述時,卻突然被抓住了,從此我再無空閑對書中的內容做任何「裁判」。我迫不及待一口氣讀完了妹妹寄來的四本書,心中只有一次又一次的驚歎:「原來如此!!!」
可以說,《轉法輪》帶給我的衝擊,比我之前讀過的所有的書加起來還大。我所有關於人生和宇宙,甚至人類社會的疑問,都在書中得到了解答。我再也不困惑了,我知道自己來到世間的目地了。我當即決定修煉法輪功。
很快的,我了解到,原來大妹妹和母親經朋友介紹,已經在一個多月前開始煉了,煉了一個月就覺得很好,所以趕快給我寄一套書來。

1998年,我在深圳一個公園裡打坐。這是鎮壓前拍的唯一一張煉功照片。(作者提供)
十七
母親和小妹妹是我上大學離開家後,才終於調到綿陽,與父親和大妹妹團聚的。為了這次調動,母親不得不放棄已從事近三十年的教師職業,和當時不算低的「教齡工資」,轉而進入法院系統,原因是綿陽哪一個學校也不肯接收媽媽,說是沒有人事編制。努力多年後,父親所在司法系統總算開恩,答應內部「解決」,把母親「安置」到綿陽市中級法院,由最低的書記員職位做起。
母親可真是個女強人,她那時已四十多歲,為了家庭團聚,不但敢於從入門級開始從事一個新的職業,並且勇敢的與女兒一起上起了大學:我上的是正規的北大,她上的是函授的全國法院幹部業餘法律大學。母親念的很努力,也很吃力。畢竟年齡大了記憶力不夠好。不過,她成績很好,幾年後順利畢業,既雪了年輕時因家庭出身未能上大學的「奇恥大辱」,職位也慢慢從書記員升到法官,直至審判長。
十八
97年時,六十四歲的父親已退休,母親和妹妹開始煉法輪功時,他不煉,也不信,但也跟她們去公園。她倆煉功,他去跳國標舞,算是鍛煉。退休後,父親就迷上了跳舞這種鍛煉方式。有一天,他跳完舞,妹妹和母親還沒煉完功,他就站在一邊等。等著等著,他自己說,他突然看見了(存在於另外空間的)法輪,足有游泳池那麼大!
在這種「眼見為實」的景象的衝擊下,父親也開始非常投入的修煉法輪功,並時不時跟我們分享他的天目又看見甚麼了:比如他看見自己煉第三套功法,手臂上下運動時,有成串的小法輪跟著上下運動。他描述說,這個「成串」,就是舊時候用的銅錢那樣穿成串的感覺。
父親說起這些時,帶著一種小孩子分享秘密時的天真和喜悅。我和妹妹交流說,也許是因為父親天性中純樸的一面未受污染,所以才會一修煉就開天目,就看到這麼多超常的東西吧。
又過一段時間,父親專門打電話來,告訴我他的老花眼好了!
他說,他現在雖然退休了,但還是被返聘回去辦些案子。有一天他整理辦公桌,看見許多碎紙片。他一邊收拾一邊想,哪個小孩這麼淘氣,把報紙剪的這麼碎?
突然,他發現,自己居然看見了報縫裡的小廣告上的字!
這種報縫小廣告的字體特別小,以前不戴老花鏡,是絕對看不見的,而現在居然裸眼看見了?
他怕這只是一時的,所以沒敢聲張。
第二天,他對自己進行測試,看是不是不戴老花鏡還能看見那麼小的字。結果跟前一天是一樣的。
他連續測試半個月,才敢確認老花眼確實好了,不需要老花鏡了,這才高興的打電話告訴我。
不過,他又特別補充道,因為修煉人講究去除執著,不能生出歡喜心、顯示心來,所以這事兒除了跟家人和煉功點上的輔導員私下講過外,他並沒有到處張揚。
十九
老花眼好了只是修煉後父親身體變化的一個方面,其他的變化還很多,比如他的血壓,以前一直很高,高壓經常是200多,常年靠降壓藥維持,但還是經常出現險情。有一次他與母親一起騎自行車出去,母親在他後邊,眼見他騎著騎著一頭就栽倒在地——原來是血壓太高引起的昏迷。當時把母親嚇壞了,從此再也不許他騎自行車。
修煉後,他的血壓很快恢復正常,再也不用吃降壓藥。慢性咽炎、鼻竇炎等許多毛病也都好了。
98年夏,我帶女兒從北京回四川探親。見到父親時,我大吃一驚:他看起來至少年輕了十歲!
在我記憶中,父親從來沒胖過,永遠是骨瘦如柴的模樣,臉上的皺紋因此很深。他謝頂也早,三十多歲頭頂就開始禿,不到四十歲,就有小孩叫他「爺爺」,他一直以此自嘲。

93年10月,父親六十歲生日照。頭上的假髮是我工作後給他買的禮物。他收到後一直戴著。(作者提供)
煉功後,他體重增加了十多斤,臉上的皺紋自然被「長平」許多,所以乍一看,就覺得他年輕了不止十歲。
再過兩天,我發現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那就是他走路時的體態。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絲》中有一個情節一直讓我記憶猶新。書中的「壞蛋」,也就是奸污了女主人公苔絲的亞雷‧德伯在與苔絲分手近四年後,變身為一名牧師。有一次他正在布道,苔絲突然看見他,並十分驚訝於他的變化,而他顯然還沒有認出外貌和衣著已大改的她。她不想讓他認出自己,想轉身悄悄走開。
可是,她不走動還好,她一走路,他立刻從她的走路姿態中認了出來:這是苔絲!
從這個細節中,可以看出,一個人走路的姿態是非常特別的,甚至比他的外貌和衣著打扮更能代表他。
所以,當我看到修煉一年多後的父親的走路姿態時,心中的訝異不亞於聽他說自己的老花眼好了。他的步伐完全變了,不再像以前那樣拖泥帶水,暮氣沉沉,而完全可以用「身輕如燕、步伐矯捷」來形容。
我能看出來,這種改變,是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唯有特別熟悉他的親人,才能一眼看出來。而這種變化,又只有在生命很深的層次、深入到細胞以下的層次發生了質的改變時,才會發生。
二十
我還看見父親在家中書桌的玻璃板下,壓著兩張照片,一張是他修煉前骨瘦如柴、老態龍鐘的樣子,一張是修煉後腰板筆直、面龐豐滿的打坐的樣子。兩張照片旁,還有他手書的一首小詩,我記得最後一句是「再苦再難永向前」,表明他修煉的決心。他說,只要一有客人來,他必定讓客人看這兩張照片,說這是弘揚法輪大法的最佳材料。
我從未看見父親那樣開心過、驕傲過、話多過。在那一個夏天,父親跟我說過的話,比他這一輩子中都要多。
二十一
可惜,好景不長,99年7月,對法輪功的鎮壓鋪天蓋地的開始,在我還沒完全反應過來之前,就已身陷囹圄好幾次。
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嚇壞了,在多次勸我放棄修煉未果後,婆母想到我父母。她認為是我父母讓我修煉的,因此只有他們才能讓我放棄。她打電話跟他們溝通。我不知父母是怎樣跟她說的,不過顯然是沒有如她所願。婆母放下電話絕望的叫道:「我到四川去跟你父母拼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一方面真怕她失去理智從北京跑到四川找我父母哭鬧,一方面又痛徹心肺的想:「您要真的不想活了,為甚麼不去找江澤民拼命!」
婆婆退休前是個婦女幹部,文革中也曾被揪到臺上「坐飛機」、挨批鬥,之後一家人不得不逃到鄉下躲避。對中共殘暴的深切體會化作她深深的恐懼和臣服。她很難原諒、也很難理解我為何不能夠跟她一起恐懼、跟她一起接受「胳膊擰不過大腿」這個理。
二十二
99年秋,我聽功友說,原法輪大法研究會幾名成員就要被開庭審理了,他們的罪名之一是「煽動」1999年4月25日的萬人上訪。那天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信訪辦外集體請願,我是其中一名。我想到法庭上去作證,說那天上訪是我自己要去的,沒有任何人煽動我。
父親知道我的想法後告訴我,這是徒勞無益的。綿陽市司法局曾召集市裡所有律師,傳達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政策,主要內容有:
1、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不同於一般刑事犯,因此雖然一般的刑事犯可以由律師出面保釋,但法輪功學員一律不得保釋;
2、法輪功學員大方向就錯了,因而在法庭上辯護時,不得像其它案件一樣,去摳公訴人的甚麼證據充分不充分、事實確鑿不確鑿等「小問題」;
3、律師辯護狀必須上交給有關領導審批,在法庭辯護時,只能照審批過的辯護狀作書面辯護,不許說辯護狀之外的話。
父親的傳達沒有讓我感到意外,但99年12月26號那天,我還是來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準備去旁聽庭審。然而,街上早已布滿警察,我與其他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一樣,連法院大門的影都沒看見,就被抓起來了。
在被送到看守所前,我們曾問派出所片警:「你估計這次得關多少?」
片警答:「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等上面的精神」,這才是中共所謂法治的「精髓」。在獄中,曾有功友問我:「你父親是四川省十大律師之一,為甚麼不讓他給你做辯護?」
其實,不光我父親是四川省十大律師之一,我母親那時也已做到綿陽中級法院的審判長,大妹妹則是綿陽涪城區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可是這些有甚麼用?鎮壓後,大妹妹因到北京上訪,被開除公職、黨籍,還上了公安部全國通緝的黑名單,父母則處於被軟禁的境地,不但經常被找去談話,在他們住處的樓下,還安排了專門的眼線,父母的進進出出,都有中共密探記錄在案。

99年初,我與母親的合影。可惜當時覺得一切都會是「天長地久」的,會永遠都那樣、永遠都在那裡,因此竟然沒想到要跟父親也合個影。那時絕對想不到,我從此再也沒機會跟父親合影了!(作者提供)
二十三
我於2000年4月第四次被捕,之後判了一年勞教,送到北京女子勞教所。無論是父親「十大律師」的地位、他的「1+1永遠等於2」理論,還是我的「北大才女」光環、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身分,都未能阻止這一切的發生。父親讓我學理時,一定以為學理科可以讓我避免重蹈他的覆轍。哪知道「計劃趕不上變化」,煉功修心,也居然招來大禍。
在勞教所的每一天,我都在目睹或親歷種種慘絕人寰的反人道、反人倫和反人類罪行,在空前慘烈的野蠻摧殘、心靈交戰和意志鏖戰中,無數人無數次的被逼到徹底崩潰的邊緣。
在這個邪惡程度甚至超過納粹集中營的地方,每一天都是生與死的交戰。在經歷了九死一生的慘烈後(詳情請見拙作《靜水流深 》),我於2001年4月獲釋。為避免再次被抓到洗腦班,獲釋後我只在家待了五天,便踏上漫漫流亡之路。
這時,我了解到,遭通緝的大妹妹「潛伏」在成都一家小酒吧打工,因為不敢出示身分證、不能辦理暫住證,已出過好幾次「險情」。那個小酒吧不能再待下去。我決意幫她逃到更安全、更妥當的所在。
我坐火車來到成都。妹妹打工的小酒吧真是只有巴掌大,而且只有她一個服務員。她每天要忙到深更半夜,等所有客人離開後才能將桌椅挪開,勉強打個地鋪睡在地上。
這樣的狀況,她當然無法「招待」我。我們只好找了個小旅館住下。一年多沒見,我們有太多的話講,整談了一個通宵,到天亮肚子餓了,想出去買點吃的,一出門就碰到一個人,他看到妹妹後臉色一變,扭頭就走。
這人是妹妹十年前的同學,正在成都當警察,顯然知道公安部懸賞三萬元通緝妹妹之事。
我們馬上退房離開。妹妹無處可去,只能再回小酒吧,我則決定「潛回」距成都兩百多里的綿陽,一來探望父母,二來從那裡幫妹妹聯繫個去處。在當時的情形下,敢於接納「通緝犯」的人不多。我只能在之前認識的功友中「搜尋」。
二十四
見到分開才一年多的父母,我像98年夏見到父親時一樣吃驚。只不過,這一次的吃驚是「反方向」的,不是驚喜,而是既驚且痛。
父親再次變成瘦骨嶙峋、沉默無言的老人。比外表的變化更可怕的是,透過他黯淡無光的臉,我看見他的靈魂已萎縮成一小團,像風乾的桔子皮一樣,沒有了任何生命力。一年多前那個神采飛揚,到處驕傲的說「我們家五口人,四口都煉法輪功」的父親,再也看不到了。
中共來勢凶猛的鎮壓把他嚇壞了。他已停止修煉,不再與我討論任何有關修煉的事,甚至也沒問過一句我在看守所和勞教所的遭遇。也許是他不敢問,也許是他沒興趣問。對於一個靈魂已被風乾的老人,這兩者間又有甚麼區別呢?
我只聽他喃喃的念過一句:「我已是快七十的人了,經不起折騰。把我的房子沒收了怎麼辦?不給我發退休工資了怎麼辦?」
母親的兩鬢,則增添了許多不曾有過的白髮。以前跟人說起她的三個有才有貌有出息的女兒們,母親的聲調總會立刻提高八度,要多自豪有多自豪。現如今,兩個女兒成了黨的敵人,隨時會淪為階下囚。母親的自豪勁兒,再也提不起來,她也像是被霜打過一樣,整日都蔫蔫的。
二十五
由於我和妹妹的特殊處境,彼此聯絡非常不方便。我當然不敢用家中的電話或手機直接聯繫她,那樣立刻會為她招來殺身之禍。我只能用公用電話打她的傳呼機,然後站在原地死等回話。她接到傳呼後只能在可以從小酒吧中抽身時,找不同的公用電話回打給我。
克服了種種困難,我數日後終於找到可以投奔的去處。我跟妹妹約好,讓她從成都起點站幫我也買好火車票,這樣才能有座位,等火車到綿陽站停靠時,我用站臺票上車跟她會合,一起北上逃走。
到了預定離開那晚,我如約到了綿陽站,妹妹卻沒有像說好的那樣下車接我。
我感到不妙,還是硬著頭皮用站臺票上了車,找到原本應該是我倆的座位,卻發現那裡坐著兩個看起來像是農民工的人。我向他們打聽上車時有無見到一個長得如此這般的人,他們驚慌失措的一口咬定:沒看見,我們一開始就坐在這裡的!顯然他們怕我說這兩個座位不是他們的,跟他們搶座位。
我不得要領,只能在擁擠的火車上擠來擠去,從車頭擠到車尾,來來回回找了一個多小時,直到火車開到一百多里外的下一站,還是不見妹妹的蹤影。
萬般無奈中,我只好補張票下車。這時已是凌晨三點,陌生的城市一片漆黑,下著滂沱大雨。我無處可去,無計可施,心比鉛還要沉。
我不甘心一人離開,又打出租車回到父母家。沒有妹妹的確切消息,我往哪裡去?
一進門,就見地上扔著好多行李,母親散亂著頭髮正在整理。
她看見我,也沒問我為何回來了,只呆呆的說:「你妹妹昨天被抓了,這是她的行李,你妹夫剛從拘留所取回來的。這是在她身上搜出來的東西的單據。」
單據上赫然寫著:法輪功書籍若干本、去太原火車票兩張、火車站行李寄存票一張,等等。
我看著滿地的行李,拿著那張單據呆在當地,大腦停止了思維。父親一把拎起我的包,強行將我推出門外,奮力吼道:「快走!別等警察問出準備與她同行的是誰!」
我愣了一愣,望了望母親斑白的兩鬢、乾枯的雙眼,和一年多來不知衰老了多少的臉,咬咬牙轉身走了。
二十六
後來得知,果然是那天我和妹妹在小旅館迎面碰到的那個警察同學為了三萬元懸賞金出賣了她。他向公安報告後,成都、綿陽兩地警察聯手,我這邊在綿陽幫妹妹聯繫去處,他們那邊一連數日在成都展開地毯式搜查。妹妹準備離開那天,已從酒吧辭了工。她先把行李寄存在火車站,因離火車出發還有幾個小時,就想去跟之前一直不敢見面的幾名同學朋友告別,並講法輪功真相。哪知功虧一簣,在公共汽車上被抓住了。
在公共汽車上抓住妹妹這個細節,是母親在綿陽《法制報》上看到的。警察抓住「要犯」,當作好大一件事,寫了長篇報導,在報紙上邀功。
我很難想像警察們在常住人口多達一千多萬的成都,到底動用了多少人力,才能在妹妹臨時起意、隨機乘坐的某輛公共汽車上,準確的將她「定位」。
二十七
幾天後,我孤身逃到太原,接應我的人按原計劃帶我去了五臺山。我站在山頂,想著本應站在我身旁的妹妹,看著滿山遍野「人雜叫賣鞭炮鳴」(1)的與佛國世界的莊嚴毫不相干的「熱鬧」景象,聽著出售紀念品的商店裡的錄音機放出的誦經聲,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愴,突然充斥在胸,逼得我珠淚滾滾而下。神佛的殿堂和聖典被人用來做了無數次的金錢交易,而真正修行之人卻在茫茫天地間找不到棲身之地。
不過,當我為妹妹落入魔掌而心痛之時,卻永遠不曾想到,父親將我推出家門的那一刻,竟會成為我們的永訣。(未完待續)
(兩億人「三退」全球有獎徵文大賽公告
http://www.epochtimes.com/gb/15/4/29/n4422842.htm)
文章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