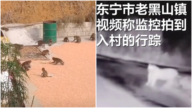【新唐人2014年5月7日訊】5月5日晚上8點來鍾,我剛從深圳回到廣州東涌鎮我家的小區門口,就被兩個穿便衣的人堵住,說他們派出所的領導要找我聊聊。我說叫他來這裏吧,我累了,不想動。一會來了一輛警車,又說要我去派出所。
我說之前你們領導不是答應了過來的嗎?便衣說去去吧,就半個小時的事。當時我老婆也在小區門口,她剛逛街回來,我就把行李交給她,要她先回去做飯。到了派出所,先讓我在大廳里等了約半個多小時,然後要給我做筆錄,一個輔警和一個穿便衣的國寶帶我到問訊室。
說是問詢室,其實是審訊室,審訊室中間設了一道鐵柵欄,審訊人員坐在鐵柵欄外面,被審訊人坐在鐵柵欄裏面。他們要我進到鐵柵欄里去,坐到那種可以把人鎖住的鐵椅子上,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你們連傳訊證都沒有,我幹嘛要坐到那裡面?他們說根據法律規定可以對我進行口頭傳喚,傳喚就是要坐到那裡面。
我說你拿法律來給我看,法律上說了傳訊要坐在鐵柵欄裏面、坐在那種審訊椅上嗎?現在有點冷,我只穿了一條長褲,我不坐那種椅子,也不進去。我堅持下,最終他們沒強行讓我進去,只是坐在靠鐵柵欄的門口。這時老婆打電話來,問怎麼還沒讓我走?不是說了半個小時嗎?我說警察的話哪能信呢?她又問到底要多久才能走?那個國寶就說今晚別想回去了。老婆問要不要送飯來?我說送來吧。
開始做筆錄了,他們說現在以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的理由對你進行傳訊,希望你配合。我要求做筆錄的人員出示證件,穿警服的輔警出示了證件,國寶就不肯出示。我說你們這不合法嘛,按規定做筆錄必須由兩個警察來做,你們一個是輔警,沒資格做筆錄,還有一個連證件都不出示,更不合法了。他們說在派出所里還有什麼好懷疑的。我說那可說不清,你們一貫是出了事就說是臨時工乾的,推卸責任。
問訊時,我基本上是回答「不知道」、「忘記了」、「這個問題我認為與你們傳訊的理由無關,拒絕回答」等,尤其是問到關於工作、家庭的事,就說這是隱私,不能告訴你們。只有一些我認為說了對我會有利的事我才說,比如,我告訴他們,我已經買了次日去長沙的高鐵票,要過去上班。
這意思是告訴他們不要太為難我,要是把我工作搞丟了,就是把我逼上絕路。其中問到我找人製作歌曲的事情,我說這事已經被你們攪黃了,那個製作人都不敢搞了。他們說那你還準備做嗎?我說我自己做不了,要不我早就做了,用不著找人做。反正我的那些歌譜早就發到網上了,誰願意做誰就做唄。
九點多做完筆錄,我不肯簽字,然後他們叫我在派出所大廳里等。九點半老婆來送飯,我吃得特別香。老婆把派出所人員數落了一通,之後先回去了。
後來一個警員拿了一張傳訊證要我簽字,我說怎麼只有一張,不給我一份嗎?他就說那就再列印一份吧。可是等了好久也沒拿來。
快十一點的時候,他們又說還要再做一份筆錄,我估計是因為我要求把傳訊證給我一份,他們不得不謹慎,覺得有些問題還沒問到,需要補充。他們又問了我去南方報社的事情、去香港的事情,還有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事。不管他們問什麼,我還是之前那個策略,要麼不回答,要麼不按他們的意思回答。比如問我和誰去的香港,我說很多人,那天一起過關的估計有上千人吧。做完筆錄我照例不簽字。
之後他們就讓我坐到大廳里等候發落。我估計不會拘留我,最多只是控制我幾個小時,折磨我一下。
期間,一個叫阿釗的輔警一直陪著我聊天。他想找話說,卻又不知怎麼說,有點語無倫次、含含糊糊。大意是知道我是個好人,但他也沒辦法。我說我不怪你,你能不作惡就不錯了。他又說知道國家是有很多問題,但不是一下就能改變的,要慢慢來,不能急。
我說那要怎樣慢慢來?當局有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什麼時候做到哪一步?最終達到什麼樣的目標?他又說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是有些問題的。我說凡事都沒有十全十美的,但有一個界限。一個國家的制度必須滿足幾個基本的條件,在這個界限之上,就會越來越好,在這個界限之下,就會越來越差。我們現在言論自由都沒有,選票都沒有,又只有一個政黨,這樣就只會越搞越差。他說不過我了,就只好附和。
直到凌晨三點才放我走,被控制了七個小時。輔警阿釗開車把我送到小區門口。走的時候也沒再拿傳喚證來讓我簽字,估計是不敢給我,怕我拿了去找他們的麻煩。
整個過程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客氣的,沒有用強硬、呵斥的語氣跟我說話,也沒有收繳我的手機。
早上我七點多鍾起來,送小孩去幼兒園,然後又去廣州看望了范一平老先生,他因為我製作歌曲的事業受到牽連,前些天在一個星期內兩次被傳喚,每次都將近24小時,害得他腳都站腫了,還抄他的家。但范先生一直很堅強,他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