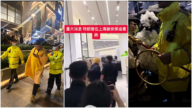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訊】本文寫作緣起
11月15日,原供職於《南方週末》的笑蜀以本名陳敏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Why China Won’t Listen,意譯應為:中國政府為何不肯傾聽有關人權的批評聲音。
笑蜀的文章有幾個要點:一,他認為,國際社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等於向中國政府臉上扇巴掌,傷了中國政府面子。這種壓力不僅不能迫使中國政府讓步,反而會幫倒忙,導致受迫害者處境惡化,他用來說明的例子是他本人被南周解聘與陳光誠的處境惡化。二是告誡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涉人權問題時要講究技巧(比如私下解決),還要讓北京感到解決問題對其有幫助。
笑蜀提到的第一點,緣於他本人的感受,我相信他這種認識發自內心,否則也不會冒著被批評的風險一吐為快。至於陳光誠的情況,其實是臨沂當局從來就非常不人道地對待陳光誠,並非外界關注才使陳光誠的處境惡化,我相信陳光誠也未必同意笑蜀代他如此立言。笑蜀提到的第二點,則是因為他不瞭解美國人權外交產生及其後失敗緣於外部條件變化,更不瞭解北京用金錢「團結」了不少發展中國家,導致聯合國人權機構功能癱瘓等事實。考慮到解惑釋疑比批評人更有實質意義,我準備在此文中向讀者貢獻自己多年的觀察經驗。
近十餘年以來,中國的人權狀態並非朝向改善直線前進,有時原地踏步,有時處於進一步、退兩步的狀態。有時因為某些特殊事件,更會出現大規模抓人的情況(如今年受阿拉伯之春影響擔心中國爆發茉莉花革命)。這時候,國內的受迫害者及其家屬,包括其他異議維權人士,在國內發佈消息都不可能的情況下,都會通過一些海外管道發佈消息,向國際社會呼籲,最先行動起來的往往是相關的一些海外異議色彩的網站及人權組織,然後是消息從中文世界向非中文世界擴散。這是國際人道援救的第一步。如果受迫害者連非中文世界都進不去,國際援救無從談起。至於國際援救的力道為何越來越弱,則需要從三方面瞭解情況。
一、美國為何放棄了「人權外交」
笑蜀在文中建議,美國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打交道時,要讓中方覺得有利可圖。這種想法倒也並非出自他的幻想,因為這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對華展開「人權外交」的基礎。但當時美國手中握有一張王牌,其時中國還未加入WTO,需要美國國會每年通過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議案。當時,「中國製造」的最大市場是美國,最惠國條款於中國出口行業利益攸關,美國即以此為籌碼,迫使中國改善人權。北京為了獲得最惠國待遇,被迫作出改善人權的姿態。最「經典」的做法是每逢國會開會討論中國最惠國待遇前夕,就釋放一至兩個著名的異議人士並將他們送至美國。當時香港雜誌多有諷刺中國當局將本國異議人士當作交換經濟利益的「派利是」漫畫,讓人看了哭笑不得。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之後,美國事實上已經失去了人權外交的籌碼。這時如果美國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做交易,只有拿出中國亟需的軍事技術與禁止對華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這對中國來說很合算,因為抓幾個本國子民做交換的人質,北京毫不心痛,且可以源源不斷製造這等「資源」。但對美國來說就很不合算,因為每一點技術進步,都是美國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結果,尤其是軍事技術還有關國家安全。加之布什政府上台執政的當年,美國還發生了911事件。出於反恐需要,美國需要與中國緩和關係。在此背景下,對中國已無約束作用的「人權外交」日漸淡出,中美兩國舉行的人權對話越來越多地流於形式。
二、國際人權組織備受北京困擾
按照機構功能設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06年以前為人權委員會)是負責審議評估各國人權狀態的機構,有權譴責那些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並提出制裁建議。但多年以來,中國通過「經濟援助」收買那些擔任理事的發展中國家,配合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搗亂,使人權委員會無法通過任何譴責中國的決議。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Felice Gaer)曾接受中國人權組織的採訪,詳細講述了中國如何竭盡心力、投入巨大金錢,採用各種方法把人權委員會變成近乎無能的機構:在人權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無法對中國指名道姓地直言譴責、無法通過任何針對中國的決議;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NGO及小國政府,讓它們保持緘默;中國很善於利用自身做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並利用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這種情況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甚至不能就中國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權侵犯表態,終至喪失聲譽,迫使聯合國不得不將人權委員會改組成人權理事會。在改組過程中,中國政府在小國之間縱橫捭闔,發出的聲音特別響亮,其目標就是要限制這一新機構的審查功能,使之成為一個於北京而言的「合作性機制」。(參見「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的交手:聯合國的迷宮」 ,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
前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特別顧問艾米•加茲登(Amy Gadsden)根據親身經歷寫過一篇「對抗、合作、倒退」(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談到自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會確立了從人權到法治的方針之後,在2000年至2010年,美國從言辭到現實直接資助中國的人權與法治項目。為了讓中國政府放心,這些項目選擇了政府機構、人大及其他中國政府信得過的機構。但到了2005年,中國國家安全機構認為,這些合作項目是美國安放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目的是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使這些合作無法進行下去。
這兩篇文章道盡了國際社會推動中國人權進步的艱難。笑蜀認為國際社會不講技巧,不謀求私人解決,是因為他完全不瞭解國際社會在推動中國人權進步上歷盡的艱難。
三、個人應該如何謀求國際援助
在介紹完大背景之後,再回過頭來談笑蜀文中的第一個主要觀點,即國際援助是否會導致個人處境惡化。
這一點確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有幾個關鍵因素因時因人因事而變化,所謂「因時」,指的是國際國內形勢,一般來說,國內外形勢不太緊張、中國當局感到的壓力不夠大時,異議維權人士的活動空間會相對稍大一些。其餘就因人因事而成,結果是:甲用某方法可能成功,而乙用則不成功甚至效果相反。
據我多年觀察,一是與被迫害者本身受到的國際關注程度有關。有時受迫害者名聲不一定大,但事件發生時,正好同類事件少,國際社會關注力度就大。有時由於受迫害者過多,這時候所謂「名人」得到的關注就多些。但在任何情況下,受迫害者不管是不是名人,僅僅只是受迫害失去工作,得到的關注程度有限,最多就是媒體關注,很快就成過眼煙雲。原因很簡單,除了香港人比較瞭解在中國的體制下失去工作是「卡住異議者的胃」之外,歐美國家的人士不會太將失去工作當回事,許多記者與NGO的工作人員本身的工作就處在流動狀態中。
二是個人受迫害的原因與其在國內所居住地點有關係。這點以前美國國會邀請我參加聽證前,專門發函要求我解答中國的人權狀態是否有地域區別,我根據自己研究過的不少案例,認為確實有,比如甘肅、湖南就與廣東、北京不相同。在甘肅與湖南這些相對封閉的省份,一個人看香港雜誌、收聽自由亞洲電台、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等,均有可能被地方當局搆陷入獄。但在廣州、深圳看香港雜誌,根本不會構成任何入獄的罪狀;同理,在北京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也不會構成入獄的罪狀。這與地區的開放程度及地方政府官員的眼界有關。
三是被迫害者家屬具有的眼光與施救過程中的動員能力與公關能力。如艾未未母親那樣的外部條件,以及本人的見識與能力,大多數被迫害者家屬並不具備。許多人在公安或者國安的恐嚇下,擔心親人處境惡化,停止向海外呼籲,錯過最好的向國際呼籲的援救時機。待回過神兒來,國際社會的眼光早被其它的案例吸引過去,而國際社會的關注眼光是種資源,這種資源是有限的,投放在哪個目標,以及投放多少,看似隨機,實際上與受迫害者親人及其「圈子」的媒體動員能力、與海外相關NGO的溝通能力都有極大關係。
四、中國的人權進步需要內外合力
在中國本土,人民爭取人權受到強力壓制,甚至人權的普適價值也被歪曲到只剩下吃飽飯的「生存權」,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助。政治學家凱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提出了「回飛鏢模式」(Boomerang Pattern)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或政府拒絕對本土公眾的壓力作出正面反應時,來自國外的一些活動家或國際組織因基於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念,可以利用各種渠道與輿論向有關國家的政府施加各種壓力,並迫使該國政府做出相應的反應,調整政策。如果本土的社會活動家與國外媒體及社會活動家建立聯繫,就會產生一種明顯的「回飛鏢效應」,即繞過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壓制,通過國外渠道向該地的上層決策者施加壓力,用中國流行的話語來說,是出口轉內銷。
這種「回飛鏢模式」至少產生幾個作用: 第一,可以及時向世界公佈中國人權狀態的各種消息,使中國政府迫害人權的劣行與反迫害的抗爭處於透明狀態,形成一定的輿論壓力;第二,通過國際人權組織的推動,借輿論壓力說服或迫使各國政府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形成外交壓力;第三,可以讓中國國內的人權活動人士感到自己有強大的奧援,不是在孤軍奮戰。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