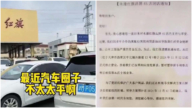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月24日訊】昨天喬遷之喜,意外地從舊衣物裡重獲失去多年的那只翡翠戒指,望著它,文革時那股辛誜血淚湧上心頭,望著它,朋友的囑託至今還瀝瀝在目,逼使我提起筆來,將廣西大屠殺這段人間慘劇記錄如下:
學習殺人
那是1968年春夏之交,廣西蒼梧縣人和公社奉上級指示,派公社人武部長黎植啟到廣西賓陽縣參加盧墟殺人現場會議。大會開始,賓陽縣革委主任指揮民兵用木棍扁擔和鋤頭一次將47個階級敵人活生生打死。會後廣西革委會要求各縣貫徹執行盧墟會議精神,以公社為單位按人口多寡分配殺人任務,大公社殺 30到40人,中等公社殺20到30人,人和公社屬山區小公社,計劃殺10人。因歷次政治運動殺人比較徹底,加上三年人為造成的大飢荒餓死萬多人,所剩五類分子寥寥無幾。黎植啟等向大會提出要求把任務殺10人落實到殺7人。
大會決議:全省統一行動:殺時禁止響槍,用扁擔木棍或鋤頭活生生打死,以此警告民眾,誰反對共產黨或不聽共產黨的話,誰就沒有好下場!從此廣西省掀起了一個大規模殺人運動高潮。
那時我從城市中學下放到人和中學任教,結識一位叫覃儒的老師,人和流山大隊人,45歲,廣西梧州師範中專畢業,任小學教師15年,教學認真負責,在群眾中享有極高的威信。為了教好學生鞏固學額,他不辭勞苦晚上進行家訪,碰到有困難的學生就慷慨解囊,或借錢為學生註冊,或資助學生交學費,讓學生完成學業,深受學生和家長愛戴。但共產黨認為這是拉攏腐蝕群眾一種手段。因為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群眾擁護他就等於擁護階級敵人,貶低共產黨的威信,必須把他的威風打下。每逢政治運動到來,都給他戴上“腐蝕革命群眾”的大帽子,勒令他徹底坦白交待。
四清運動禍從天降,一些村幹部為了立功,栽贓嫁禍,污蔑他私藏武器,勒令他停職反省,徹底交待問題。
他說:“我一介書生,少年在人和中心校讀小學,畢業到龍墟讀初中,之後到梧州師範讀中專,1952年畢業,回流山小學任教直到現在,哪來的槍枝?”
那幹部頂證說 :“我親眼見你父親背著步槍上山打獵。解放後那支槍藏到哪裏去?”
覃儒說:“解放前有錢人家為了防範賊人搶劫,都買枝槍看門口。那時我離開家庭,去人和中心校讀小學,不了解情況。究竟是父親的還是借人的?我實在不知情。後來父母相繼去世,也沒有留下遺言。”
幹部追來追去,沒有結論,便把它挂起來。文革運動一到就找他算賬,勒令他徹底交待槍枝下落。在大隊部鬥爭時少不了吊打跪,就像斗地主那樣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今次清理階級隊伍,一定要他把槍交出來。
推廣殺人
人和公社革委會在人武部長黎植啟的領導下,先回蒼梧縣集訓,學習消化盧墟會議精神,出大字報互相檢舉揭發,掌握內部情況,培養積極份子,佈置工作任務,然後從外部入手,將七個五類分子抓起來試刀。會議決定回到公社後分頭做好工作。一個禮拜後(即八月十六那天)召開公社社員,學生,教師和幹部大會,地點公社門口廣場。
教師集會,覃儒深恐大難臨頭 要求我不要和他接近,以免影響自己的前途。但我認為朋友有難就一腳踢開,是做人沒有骨氣的表現。我對他說:“不要怕,有甚麽就說甚麽,不要為了過關就認罪。放心睡覺吧,天塌下來當被蓋。”
次日天未亮就吹哨子起床。漱口梭洗完畢,所有教師集中到校園開會。校園四周被教室圍著,一個路口出入,由民兵卡守。只准入不准出,會議開始由黨支書鄒德光講話。他宣佈當天上午10時集中到公社露天廣場開會,禁止帶鐵器刀具進場,違者當破壞會場論處。老師要管教好學生,只准看不準動,不准交頭接耳和喧哇大叫,看完後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有問題的要徹底交待問題,爭取從寬處理。會後不准喧揚,違者後果自負。
教師聽了不寒而慄,個個緘口結舌,你眼望我眼,彷彿大難臨頭。吃過早飯,教師率領學生列隊到公社露天廣場集中。那裏席地而坐滿了人群,圍成一個巨大圓圈,最裡面的是民兵,民兵的外層是居民,居民外層是青少年學生,被最外層的教師管著,不得隨意走動。這是有史以來最多人的一次集會,神情驚恐萬狀。像死一般的寂寞。
10時30分大會湊起毛澤東語錄歌。歌畢,十多個衛紅指揮部的民兵押著7個被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步入會場,人武部長黎植啟命令他們相隔一米背對背跪下,任何時候不准調頭觀看。接著從後面衝出一條大漢,他手提夾木棍,滿臉通紅地怒氣沖沖走到一個五類分子跟前問:“你認識我嗎?”那五類分子道:“認得認得,那是村民意見,偷雞挂牌遊街是他們所為,不關我事。”李錦雄道:“你出口他們出手,主犯是你。”說完一棍朝五類分子頭部打去。那五類分子側身避過,打中肩膀倒在地上,李錦雄趨步上前朝頭狠命一棍,五類分子顫抖著兩條腿,一命嗚呼了。 為了穩定其餘六人,李錦雄指著死者說:“你詐死,等會兒再跟你算賬。”
李錦雄轉過身來跟一個打鐵的五類分子說:“你打關刀和匕首是否伺機反攻倒算,顛覆無產階級政權?”那五類分子連忙說:“不敢不敢!我只是賺點錢養家活口罷了,哪裏敢胡思亂想,違反政府法令?”李錦雄揮起木棍當頭狠命一棍,“卟”的一聲響,正中要害,就像開了個油醬鋪,咸的,酸的,辣的一發滾了出來。再補一棍便伸直兩腳氣絕身亡了。
其餘五個階級敵人被民兵監視著,不准調頭看,但聽得真切木棍打人的聲音。其中一個五類分子違令,聽木棍一響,便掙扎調頭觀看,見兩個同伴被打死在地,“哇”的大叫一聲:“民兵殺人啊!”求生的欲望從跪地一躍而起,其他四人亦拔腿飛奔,守在身後的民兵見狀慌了手腳,提起木棍一窩峰地追了上去。一位上了年紀的五類分子被民兵追到,攔腰一棍打翻在地,再補一棍兩條腿伸直不動了。
另一位上了年紀的五類分子估計跑不過他們,停了下來說:“老鄉,且慢動手,讓我死個明白,為甚麼要殺我?我一向奉公守法,死不瞑目啊。”那民兵道:“這是公社黨委命令。你裡通外敵涉露國家機密,把祖國的情況告訴台灣敵人,使國家的名譽受到巨大損失。”那五類分子道:“那時大飢荒,我三天沒有粒米下肚了,向親人求救,寄些米油糖回來度荒年…”話沒說完,李錦雄手提木棍追上來,對民兵大吼一聲:“和他講甚麼耶穌!”掄起木棍照頭便打。那五類分子躲閃不及,正中要害倒在地上,再補一棍,伸直兩腳不動彈了。
其餘三個五類分子為了求生,衝出人群,奪路向大街跑去,但雙手被反綁著,哪裏跑得過年青力壯的民兵?未到第二條街口,就被李錦雄率領的民兵追上,揮舞木棍一輪毒打,三人登時斃命。
人和公社殺人現場會議前後一個小時結束,街道上血淋淋的躺著七具死屍,學生嚇得面如土色,“哇”的一聲四散奔逃。膽子大的跑到大街看五類分子遺體,有的被打爆了頭,鮮血流出地面﹔膽子小的到飲食店買粉麵吃,邊吃邊失聲流淚。老師為人師表受紀律約束不敢走動,尤其從城市下放來的老師從未見過恐怖野蠻殺人場面,嚇得心驚膽戰,呆如木佛。
覃儒老師是本地人,經歷過農村所有政治運動:如“請匪反霸”,“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大飢荒”和“四清”等運動…中共先把民間反抗力量徹底消滅,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鬥爭“國民黨舊人員”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槍奪他們的財產,把他們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管制起來,放到各個政治運動中加以殺害。今次只殺七人,其餘亦肉隨砧板,任剮任剁。
沉屍滅跡。覃儒老師望著人武部長黎植啟指揮民兵虐殺五類分子,心裡早就做好準備,他拉著我的手,端詳著我的面,久久才問:“張老師,你不怕我連纍你嗎?”我說:“怕甚麽!身正不怕日影斜,你又不是犯法,被人懷疑罷了。”
其實我的心也是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因為我大姐是美國公民,中共十多年的宣傳:“美國是中共的頭號敵人”,1960年大飢荒時父親寄信要求大姐接濟,被公安局檢查信件,在檔案裡記上“裡通外敵”,株連後代。一個禮拜前公社黨委在蒼梧縣參加清理階級隊伍大會,在龍墟的大街聯名出我的大字報,從三樓吊到地下,檢舉我是混進教師隊伍的美蔣特務。暫時未搞到我頭上罷了。
他見我態度堅決,把眼睛端詳著我,隨即從左手無名指脫下那只翡翠戒指說:“我非常願意和你交朋友,如蒙不棄,請收下這只戒指留作紀念吧…”話未說完,衛紅指揮部的宋隊長走到面前大聲吆喝:“覃儒,公社給你一個任務,將一具死屍拖下駁船!”說完將一條蔴繩拋到覃儒身上。
覃儒大吃一驚,知道把自己和五類分子等同看待,急忙將翡翠戒指戴到我的手上,拿起蔴繩問宋隊長道:“拖哪一具?”隊長道:“拖前面那個老鬼。”覃儒將繩縛在老人腳上,又將繩搭在自己肩膊上,用力往珠江河面拖。
那時珠江河氾濫,河水咆哮著衝出一個個小漩渦。覃儒拖了十來丈遠,突然被東西卡住了,調頭看時,只見那老人呻吟著,發出微弱的聲音:“你把我拖到哪裏去?”覃儒大吃一驚道:“宋隊長叫我把你拖下駁船。”那老人意識到生命到了盡頭,求生欲望使他倏然坐了起來,用哀求的聲音說:“放我一條生路吧,我是無辜的。”覃儒說:“你不能走,否則被民兵發現把你打死。你會游泳嗎?下了駁船我把你放下河裡,你自己逃生吧。快睡下,不要動。”
覃儒放開大步把老者拖下駁船,駁船早就攤著六具屍體,六個五類分子忙著把屍體的雙腳拴上大石,逐個抬到船舷,“咕咚咕咚”的推下河裡。風大浪急,河水滔滔滾滾,一棑棑一串串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虐殺的五類分子死屍(1),被浪衝到船頭,幾個民兵急忙拿起竹篙撐開,屍體滾起一團水泡,發出膿郁的臭味。駁船顛波不定,負責抬死屍的五類分子冷不防踢中老人家的活結,澠索散了開來,被宋隊長發現,重新打上死結,正想推下河裡,老人求生的本能用雙手死命抓住船舷,宋隊長用手扳不開,李錦雄見狀跑到廚房拿了一把菜刀,對準老人的手指狠命地砍下去,“嚓!”的一聲手指凌空飛起,老人“哇——”的一聲!如山崩地裂,水靜河悲。一個才華卓著的學者,被一個二流懶漢的共產黨員奪了姓命!
走上絕路
覃儒想救人沒救成,反而露了馬腳,被李錦雄告發,黨支書鄒德光勃然大怒,厲聲吼道:“你不想活了!你要老老實實坦白交代!”接著勒令覃儒停職反省,徹底交待問題。覃儒左思右想,從過去想到現在想到將來,再想到年幼的子女,自己有責任撫養他們,但現實不允許自己選擇。他立下了以死明智的決心,領了一疊原稿紙坐在辦公室裡揮筆疾書:“你要老老實實坦白交待,你要老老實實坦白交待…”一連寫了八句,每句代表一個運動到來黨委對他施暴,吊打跪逼他寫坦白交待。但他冷靜一想,這樣會激起共產黨的憤怒,鏟草除根,滿門滅絕。
覃儒為了不連纍妻子和兒女,提起筆來說理:“我是一介書生,自幼離家讀書,沒見過父親玩槍,是別人借給父親打獵的,不等於父親有槍,更不等於我為父親收藏槍枝啊。”寫到這裡他停下筆仔細讀讀,覺得重要的不寫。
於是他又拿起筆來寫下遺囑,把欠學費的五十多個學生連同家長的姓名地址寫在另一張紙上。末了,他看看手錶,時針指向十二點,他把坦白交待書壓在臺面上,把遺囑疊好放進衣袋裡,跑回宿舍,見我睡著,輕輕推我一把,我從夢中驚醒問:“有甚麽事?”覃儒道:“看來他們不會放過我啦!”我安慰他: “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吧。”順手把那只翡翠戒指交還給他。他堅持說:“留作紀念吧。如果有機會到美國,不要忘記把此事告訴世界人民。”我覺得事情嚴重,起身陪他到外面走走,勸他放開胸懷,千萬不要自尋短見。他用力握住我的手,久久才放開。取了自行車,一溜煙向流山大隊飛馳。
兩點鐘後抵達家門,他用鎖匙開了大門,看見房裡的妻子和孩子正在熟睡,他多麽熱愛這個家呀,但現實不允許這樣做,他凝視著他們,久久才轉過身到廚房取了一個瓦煲和一盒火柴,趁著月色明媚高一步低一步向前行。在路邊拔了一棵大茶根(又名斷腸草),裝了一煲水,拖著沉重的腳步向著達瓦山而來…
早上七點鐘鄒德光起床,見到覃儒的坦白書壓在臺上,肺都氣炸了,認為他大逆不道,馬上派民兵抓他到辦公室來,準備召開公社教師大會,殺一儆百,以戒萬人。可是找遍整個人和都找不著。又派民兵到他家裏搜查,他妻子說從來沒見過他。第二天發散民兵去找亦無結果,第三天一個社員反映:在達瓦山看見一個人站在一棵樹下,怒眼凸睛,一動也不動。
鄒德光派民兵打聽,果然發現覃儒挨住一棵樹站著,在日光的照耀下怒目而視,噴射出火紅的光芒(2),彷彿要摧毀這個萬惡的社會。
註:
(1) 廣西大屠殺發生在1967至1968年,殺人面積普及全省每個公社每個大隊。大部分死者挖坑掩埋,小部分推下珠江河裡,讓洪水衝出虎門流去香港,中共中央派出三個團的兵力常駐肇慶峽,佛山欄石和虎門,日夜打撈屍體,並動員沿江漁民協助,每撈得一具屍體獲30元人民幣報酬。
(2) 凡服過大茶根的人,七孔流血身亡。
(3) 此乃事實,覃儒死後不久我被打成大漢奸大特務,幾乎死於非命。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六日 張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