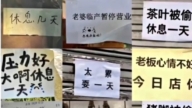「對楊佳的審判不公就是對我們大家的威脅,這是毫無疑問的。」
今天是十月二十號,楊佳的二審下來,維持一審死刑原判,你有什麼感覺?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這裏可說的太多了。表面上看上去,一個很簡單的案子,得到一個簡單的必然的答案。可是造成這個必然性,實際上是經過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層面,是整個社會整個歷史經過了很多年,經過了很多可能性,才造成了這麼一個簡單的答案。
在這個過程中,你是不是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實際上我不認為這個奇跡會存在,但是我還是覺得,人的生存,每個人的行為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個人生存的一個需求。楊佳只是在這個問題上,使我有可能闡述這件事情。也正是由於這種難度和不可能性,我才寫了二十多篇文章,自己也很吃驚,從來沒有為任何事情這樣做過。可能就是因為有這種不可能性吧。我想,如果這個事情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有其他人為這個事情在做努力,那我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去做。
這個事情,跟你以前關注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內在的關聯。它不是偶然的,比如邱興華被判死刑,薩達姆被判死刑的時候,我記得你當時的一篇文章,你對這兩個人異地被幾乎同時處死,表示了特殊的憤怒,當時那個情景我印象非常深,你能講講這三者之間的關聯嗎?
這個問題我倒是完全沒在楊佳案上談起,就是死刑的倫理問題,在楊佳案中還沒有機會談到,因為我仍然認為楊佳案是有可能改判的。當然,這個可能性現在越來越小。如果說是他判了死刑,那麼就涉及到一個死刑的倫理的問題。
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死刑在世界上最多的國家,他曾經是世界死刑總量的一半以上,此前最多的時候是達到四千多人,整個世界所有的國家是七千多。受到輿論譴責後,做了一定的改善,將死刑的復核權交給了最高院。這麼做以後,使中國的死刑少了一些。
首先,死刑本身有悖於倫理。如果說殺人者必被殺,這實際上是說,除了上帝以外,人有權力奪取他人的生命。如果說生命是至高無上的,是有其尊嚴的,那麼原則上是誰也不能踫,一個人殺了他人,你再殺他,等於是說你支持取消他人生命的倫理合法性。
回到楊佳案,死刑之前這一段,甚至說到他犯罪之前這一段,都是含糊其辭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普遍的危險。為什麼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在上海借了輛自行車旅遊,會被員警扣留,毆打,員警之後不承認,造成他在申訴了很多個月無果之後,再前去進行「報復」,那麼這個報復的過程,都沒有嚴格地按法律程式來取證,致使這個案件變成一個非常不清晰的案件。那麼是在什麼情況下,一個體制會為了遮掩一個小的漏洞,把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缺口,暴露了體制的根本問題。這是原則性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你會想到,一個明顯的殺了上海的六個員警的案件都會在它的案情上這麼不清晰,那麼在其他的案件當中,中國公檢法的程式問題,清晰度問題,會是個什麼狀況,這是我有興趣的地方。它清楚地說明瞭它缺少獨立公正的司法倫理體系。背離了這個倫理體系,法律起到的不是除惡的作用,而是惡本身。這是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在關注楊佳案的過程中,曾經想到避免死刑,從法律程式的角度來講,現在還有「死刑復核」的程式,你說在這個階段會產生奇跡嗎?
這很讓我懷疑。我試圖認為,違背法律,或者違背事情發生的邏輯,違背善,只是個人或是局部的行為,這種理解顯然是不對的,它更是一個體制一種文化的行為。因為我在想,如果整個案情發展過程中,這七個員警,如果有一個人能站出來說,我打了他,這個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在偵訊階段,如果閘北公安局進行偵訊的人,嚴格的偵訊,這個事情也不會發生。如果在司法鑒定的時候,精神病鑒定如果按程式來,按合法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也不會發生。如果當時他們能夠回避,選擇異地來審判,異地偵訊的話,這個事情也不會發生。一審的律師,如果有一點律師的貞操,有一點道德的約束,真正地為他的辯護人服務地話,這個事情也不會發生,當然還有一審的法官。二審的律師,所有的這些只要是盡了一點善心;這個事情也不會發生。你會發現,它是一個群體性的墮落。就是說要不惜一切代價,包括二審的律師,很明顯地,來完成對這個人的死刑。這實際上是很盲目的也是很愚蠢的,你殺了楊佳一個人,但是,實際上付出的代價是整個社會倫理的顛覆和錯亂。告訴所有人,在這個社會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個更愚蠢的事情。如果是媒體能夠公開的報道,新聞調查能夠做一個簡單清楚的判斷,如果有獨立的媒體,或者是獨立的司法都不會發生這些問題。這是每一個人把他推向死亡。實際上推向死亡的已經不是楊佳個人,是整個社會的腐朽結構。
我更相信,它是撕開了這個社會結構的某些真相,實際上是在整個社會的運作當中,國家機制還有各種程式之間,習慣性的採取了某些對事實的不尊重,對程式的藐視,而這一程式本身是不需要太大的代價就可以堅守的。這樣一個麻木的群體的無意識,你覺得是開始於什麼時候?是不是我們大家都有可能是一個共謀呢?
開始於當一個權力,一個結構,它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時候,那麼和他相關的所有的細節都會有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的合法性的問題。
下面,如果這個事情告一段落,那麼它所產生的後遺癥裏面,有沒有積極的因素?
這個事情不可能告一段落,它只是整個社會倫理腐敗的一個部分,它像一塊傷疤一樣永遠會在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的臉上,留在這個國家的臉上,毀滅是沒有階段的。恥辱也是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有一種說法,楊佳案反映出法庭裁定在邏輯上的一個悖論。如果承認楊佳是報復殺人,那一定有報復的原因。如果沒有原因,那他悖于常理的行為只能用精神病來解釋。是事出有因與事出無因,兩者必居其一。現在看,這是不是在程式上的一個怪圈?
這個邏輯是清楚的。這兩個邏輯都不能夠成立的話,那只能說這個做判斷的人精神上有問題,這個體制有精神病,這是很清楚的。
在二審裁決之前,律師翟建通知楊佳的姨媽很可能維持原判。
這也是很可笑的,原告還沒有出現,作為辯護律師的翟建就通知他姨媽說會這麼判,很簡單,翟建在這裏面是有交易的。這是不可以想像的事情。
記得美國有一個世紀審判的「辛普森殺妻案」,就是因為檢方取證程式上的錯誤,最後辛普森被宣判無罪。公眾看到了「證據」在司法中的嚴肅性。此案中類似的很多基本證據都沒有呈現,這個事情是不是離譜了?
不但基本證據沒有,而是公訴人毀壞或者掩蓋證據,這更恐怖。比如說楊佳的母親在哪里?這是任何一個人都要問的一個問題。不是因為任何人都有母親,而是她是重要的知情人。她如果是同案犯,那麼你必須把它抓捕歸案,她如果是知情人證人之一,也不應該消失。何況她是重要的證人。楊佳當時在警察局裏三次給她打電話,話費花掉兩百元。當時警察局發生了什麼,她是唯一知道的人。那麼把她藏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很明顯,這個案子是不用審的,第一秒鐘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實際上,審,使法律能給他們的一個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在若干個點上糾錯,但是他們沒有把握機會。誰都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他們也能在楊佳案剛發生的時候,把一個在網上寫東西的網民抓起來。這顯然是違法的。現在拘留一百多天了,這個網民現在哪里,這是依據什麼樣的法律程式來完成的?上海他們是非常自以為是的,他們認為他們是萬無一失的。但是他們錯了,因為這個時代不一樣了,人們不需要按照他們這一套程式來鑒別他們是不是違法的。
你受到過威脅嗎?
我每秒鐘都受到威脅,因為我生活在一個非常有危險性的國度裏。
具體講有沒有明顯的威脅?
對楊佳的審判就是對我的威脅,這是一樣的。不是一把刀子抵著我,才是對我的威脅。只有豬才會這樣去想問題。當一個人的尊嚴,他的生存的理由被動搖的時候,他就是受到了最大的威脅,這毫無疑問。
這個問題是否有轉機的可能?
幾乎沒有。中國的法制在過去的三十年來幾乎沒有進步,這是讓我很吃驚的,它處在了一個凍結狀態。雖然經濟發展,甚至經濟的發展也可能是靠法制不健全來完成的。前兩天,哈爾濱的員警打死了一個學生,那麼剛開始就傳得亂七八糟,播出錄像好像是學生在打員警,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全世界沒有學生打員警的事。今天播出了後二十分鐘的錄像,是當初電視台沒有播出的,是六個員警踢一個學生五六分鐘,一腳就可以把人踢死的。現在承認了是員警施暴。要在這種問題上去爭論,人被打死了,仍然要去爭論這種問題的話,何況楊佳只是被打傷過。楊佳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了,就是說凡事要有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必須給你一個說法。這是說,他曾經向這個社會討公道,但是這個公道他沒有討著,他最後用自己的行為去完成他的認知。
二審的辯護律師翟建說,證人員警是不必出庭的。
胡說八道。辛普森的案子,就是證人出庭才翻了這個案子,要不然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話,你等於說楊佳也不用出庭,那你就完全想怎麼判就怎麼判吧。這個王八還能做律師,是很奇怪的事情。他還是上海十佳律師的第一名「東方大律師」。
如果接受了北京的律師,會有什麼結果呢?
北京的這個律師好很多。當然,上海必須請自己的律師,為了避免麻煩,讓真相不在法庭上呈現出來。
楊佳沒有受到公正的審判,沒有受到最起碼的公正的待遇。那麼這是很恐怖的。如果說在公安局裏面受到了毆打,是不公正的,那麼他在法庭的待遇則是更加的不公正。如果說這個法庭是公正的話,那只能說這個社會是一個完全不公正的社會。如果社會都沒有這個認識的話,那我們連審判都不要談了。
二審的時候,上海在處理媒體的時候跟一審有區別,似乎開放度大了許多,是不是他們也感覺到了一些不妥?
不,他們從最早和最後都想的很清楚,就是把事情掩飾掉,不存在什麼不同的感覺,一審是秘密審判的,造成了很大的社會輿論,二審必須要做的公開一些,但是所謂的公開是沒有意義的,連同室都不是,在另一個房間看錄像,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公開審判。這是中國對司法公正的理解。如果這叫「公開審判」,那就等同於,中央電視台做的動畫也跟直播一樣。
這個事情在整個世界的輿論裏是不是必然有很意想不到的影響?
老實話,沒人搭理你,中國人愛死不死,沒人搭理你。這個世界也沒什麼所謂的永恆的公理可以談。這是件自己折磨自己的事。
越來越悲觀了?
沒有,既不悲觀,也不樂觀,這是我們的處境,我們必須瞭解它。
我很感動,現代藝術在當今社會中,期望藝術家在核心問題上要體現出來獨立言論和自由勇氣。跟你有相似影響和地位的人,好像集體失聲了?
我不知道。我只能從倫理上說,任何一個人,如果是不為正義而戰,不為所謂的公平而戰,他就是非正義和不公正的一部分。這毫無疑問。(完)
張華潔根據電話錄音整理,(艾未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