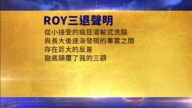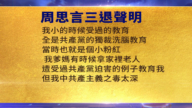【新唐人2005年10月13日】热点互动直播(27)五中全会落幕政治危機出路何方:中共政權當政,中國就無出路。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己经结束,那么这次全会是不是走过场?面对中国民众风起云涌的“抗议之潮”和“退党大潮”,现任政府应该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真正的一起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提出您的问题,发表您的高见。
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陈奎德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也是电子杂志《观察》主编;凌峰先生是著名的政评家;李天笑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博士,也是我们《新唐人电视台》的特约评论员。
安娜:首先问一下陈奎德先生先生,您对这一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总体的印象是什么呢?
陈奎德:说实在,我没有仔细研究它这个公报,凌峰先生研究的倒是比较透。我是只有三点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党越来越黑,这个会越来越僵,这个全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笑话。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笑话,那个公报没有任何内容,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所有各方的口号都拼杂进去的一个大杂烩,所以我过去也一直是不大关心中共开的大会、五中全会或者是几次党代表大会等等。
我觉得凡是它把这个会抢先预报说什么重要的,预先预报很多的,最后的情况一定是没有什么内容;但是有些会没有预报,大家都不大重视的,或者大家都根本不去注意的,最后突然爆出一个冷门来,发生了什么人事变动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中共的架构己经僵化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一个政党像这样己经非常难以想像,这是我的基本印象。
安娜:凌峰先生对这一次的全会的公报做了很详细的研究,您对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什么评价呢?
凌锋:我觉得我想看的没有,像是人事变动;不想看的,它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每一个我们想像到的问题它都会提到,都提到一句,不晓得在干什么。所以我有一个感想,任何一个中共的领导干部,在看到这一个公报以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做;如果他要做,恐怕不要说三头六臂,就是六头十二臂都做不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当然目标是很宏伟的,2010年的GDP超过2000年的一倍,但是怎么做?我看是谁也做不到,我总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安娜:天笑,有很多人像凌峰先生和陈先生他们这样的感想,觉得这次的全会是了无新意,想看的没看到,公报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信息,大家想知道的也没有。不知道你怎么看?
李天笑:我很佩服凌峰先生还能耐着性子看下去,我基本上是看不下去,但是硬着头皮看了一点。我觉得这个会分虚和实二方面。虚的就是共产党一贯大会小会,宏伟规划,这是虚的;花架子,雾里看花你看不明白,你看那个字里面,都是老调重弹,再仔细看也没有东西。但是实的东西,人事的变动、权利分的配和分贜,据说在会中遇到障碍;就是江、胡之间到底怎么安排,你上我下,你唱我罢,这样的安排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有几点在这个公报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讲的“科学规划”。什么叫科学规划,这规划原来据说是五年计划,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不用说它了,但是它换了一个字,从计划改成规划,就大肆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十个五年计划做下来以后,现在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很多。当初中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基本上在一条起跑线上,现在台湾是一万二千到三千美元的人均GDP,香港和澳门都超过二万美元,大陆现在才一千多美元,这个距离不能希望它在今后五年当中马上消弭,不可能的。
第二个它讲要社会保障系统。贪官污吏把这么多钱拿出去,它哪有钱来发展社会保障系统呢?中国的医疗、教育、卫生这些基础设施都是非常差的,在世界排名非常后面;如果说它要做一点这样的改良,也是贪官污吏巨大吞进去的财富当中吐出几口出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个它讲要农村的民主管理,那就更可笑了。在这个期间在太石村,人大代表在太石村调查被打,外国记者被围攻,同时上访的人员几千几万这么抓,和它讲的民主、和谐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总的印象来说,这次会基本上是共产党统治的巨大讽刺。
安娜:陈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全会历来被认为是中共上层权利斗争的战场,这一次很多人认为胡锦涛实际是想通过这次全会稳固自己的政权,您觉得结果如何呢?
陈奎德:据外电和各方面的观察、评论,基本上认为胡锦涛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实际上胡锦涛、江泽民的权力架构,这二、三年大家都看他们谋去谋来,争去争来,背地里、明显的都在弄。实际上很显然,胡锦涛这一次没有完全得到,尤其是像上海这个城市的主要的领导人的职位,没有得到主管这样的一个结果;已经做了好几次放风了,实际上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像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个派别己经非常清楚了,他们政治上的人脉,包括他们的政治理念表现出来也有所差异。因为胡要表现代表所谓的低层民众;而江是所谓三个代表,代表的是所谓的先进力量,实际上是比较强势的力量。
所以我倒有一个想法:中共这种己经越来越明显内部派别纠纷,不如像日本自民党这样,各自慢慢亮出自己的旗帜,亮出自己的政纲,亮出自己的人脉。尽管你现在还达不到多党治,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党内慢慢把派别清晰化、公开化、明确化,这样的话,政治有比较文明一点。
我觉得既然现在胡锦涛和江泽民的班底,包括他们的理念,都有众所周知的分歧,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了。中共逐渐的走向党内派别的公开化、明朗化,和逐渐地法治化,对党也好,对中国整个国家也好,都是一个福音;如果老是这样在一个大旗蒙着,底下搞很多小动作,既不文明,而且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安娜:我们现场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了,是纽约的杨先生,杨先生您请讲。
杨先生:台湾立法委员李敖到中国去访问时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中国现在是唐朝以来最兴旺的时候。我不知道李敖是台湾立法委员,还是倾向我们国家的,你们认为是怎么样?
凌锋:唐朝最兴盛的时期是“贞观之治”,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现在中国你看看吧!能不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个门还要加个铁门呢!
安娜:还有铁窗呢!而且一层加了二层就要加,一层一层加上去!
凌锋:治安是愈来愈坏,歹徒可以和警察谋和,这个叫什么盛世,简直不能理解,我看是自吹自擂。
李天笑:唐朝时期是万国朝拜,那是最鼎盛、最兴旺的时期;到了清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占世界的近一半左右;但到了共产党,现在只占百分之四。这么一个巨大的差距,还说现在和唐朝比,根本就不能比了。还有共产党现在的贪污腐败和唐朝的路不拾遗,整个道德的高尚等等,也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从这两件来看,共产党的领导,我要说比呢,实际上还是抬高了它。
安娜:陈先生有什么感想吗?
陈奎德:两位刚刚都说的很好。实际上简单的很,像李敖说的这种话,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身份去演讲。中国人有哪一个人,包括知识份子、学生能够公开地像他这样去说这种话?有哪一个人能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的办自己的一份报纸,办一份刊物?
现在中共把整个中国完全在新闻信息上封闭,在全世界最落后的排名国家之一。你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兴盛的国家,这不是讽刺吗?既然这么好,你让大家都来看,让所有的报纸都来报导,让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来讲,所有的电视都来播!现在封锁的这么严,你还说这个国家是这么伟大、光荣、进步、富裕,这不是讽刺吗?
只有一个标准,你让新闻打开,这个国家好不好,新闻打开自然知道;如果不敢把新闻打开,你这个国家没什么话好说,你就是完全没有现代基本文明的国家,还说什么兴不兴盛。
安娜:我想也可能像你所说的,李敖说的是反话。刚才凌锋先生谈到,这一次你想听到的没听到,那你觉得这个对外界传达的是一个什么信号呢?是不是胡锦涛目前面临很大的危机?
凌锋:我想是有很大的危机。除了刚才讲的人事调动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有些人事调动公报里不会讲,但是假设说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调动,或是从中央委员调到政治局的调动,那是要公布的;如果重大的人事调动都没有公布,就说明是胡锦涛想要做的没有做到。而且公报里面,像我刚才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句话,那等于是照顾各个方面,就是说胡锦涛想走自己的一条路,好像比较否定过去做的不对的地方,就说明他就做不到。
比如说这次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讲科学发展的话,应该在科学发展这里落很多笔墨,其他东西就不谈;但是所谓的科学发展,它在里面讲节约只讲一句,讲环保也只讲一句;如果这次主要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里面很多措施、目标都肯定要有,但是宏观调控也只有一句;所以就说明他想做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做不了他又不想得罪,也不能得罪人,又要表示自己是以民为本,所以等于就是每样东西都讲一句。但我们看来是假大空,比如说卫生医疗保健制度,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个报告出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这次你看他说要“完善医疗制度”,“完善”是已经做的相当成功,只剩下百分之几没有成功才叫完善,它现在等于是从头开始,怎么可以叫完善呢?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假大空,在欺世盗名 。
安娜:我们再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是纽约刘先生,刘先生您请讲 。
刘先生:我想问一下凌锋先生,你刚才提到没什么想看的就不去重视,我想知道美国现在是不是重视?我是觉得你们是政治家、评论家,回答一些问题的方式,好像一些家庭妇女在议论政治,没有一个评论家的这种很高的素养回答问题的方法,好像觉得共产党一塌糊涂,其他国家都是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你这种看法,我不认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安娜:凌锋先生,您能不能说一下?
凌锋:当然我也不能讲说我自己讲得如何好,我的认识里面,我觉得是它这个五中全会的确是开的不好,如果开的好的话,它不会出这么一套假大空的东西;同样美国的制度,也不见得是十全十美,也有它的问题,但是它有问题,媒体都可以提出批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国家它就有活力,它能不断的改革自己的问题,不断的进步;而中国是明明有问题,你还不能讲,那它就永远停在那里。像开发西部,缩小贫富差距,也讲了十几年啦!但结果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卖血的还在卖血,爱滋病蔓延的还在蔓延。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开放言论,能不能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李天笑:对于刚才这位观众提的问题,我也想讲几句。中国跟美国比,首先经济上当然是比不了,美国现在人均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三十三倍多,中国要赶多少年?如果说现在中国要赶上美国的话,全世界的能源,钢、煤、石油都给中国用,中国也不够用,这是在经济上讲。
在政治上讲,就更不用说。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提倡自由民主,人人都有发言权,比如说我们这节目你拿到中国大陆去播,很可能马上就给你关了,人都抓起来。在美国你随便可以讲,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等等,这些在中国目前为止都是受到打压,没有的。那么从其他的道德风尚来看,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了,可以看得出来,人跟人的关系都比较和谐,都是保持着一种三、四十年代那种绅士风度。
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都有贫富差距,美国也有很穷的人、很富的人。中国也有贫富差距,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怎么造成的?这个贫富差距是共产党藉国家的名义,掠夺人民的财产,然后变卖人民的财产,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是富起来,谁先富起来了?跟权力有关、有资源,能拿到圈地权的这些人富起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在生产市场中,交换中产生的。所以说从几个方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确实是不同,但是不同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安娜: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下一位是纽约的林先生,林先生您请讲,林先生可能掉线,那我们再接下一位的洛杉矶的苏先生,可能也是掉下去了。下一位是纽约的黄先生,黄先生您请讲。
黄先生:我讲一下。你要讲中国好也好,美国也好,说现在共产党好也好,中国大陆不好也好,实际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是觉得一块金子,这块金子上面它有几个地方是生锈的,那么大陆它实际上是一块烂铁,有某几个地方上面有几个金点,你不能够用大陆的金点来跟美国最烂的地方去比,应该整体的去比。
我们在海外的华侨都看见中国某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很繁华,实际上中国从整体来讲,它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因为我去过内地的地方,内地的地方简直是真的是一穷二白。我们不能够看沿海的城市去感觉,唉呀!现在中国大陆怎么怎么好,不能这么去对比的。之所以今天中国大陆还处于这么落后的状态,平均收入这么落后的状态,跟共产党的制度是相当有关联的,所以我也劝劝我们有些海外的华侨,应该从全面的去看一个国家的好坏。
不要说其他的,我们就刚才那位先生讲的,就从他本人来讲,他今天来到美国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中国的落后给造成的。有的人也会说:我来美国不是为政治来的,我是团聚来的,或者是其他原因来的。但是为什么你要来美国团聚,不能到中国大陆去团聚呢?在这之间很大的问题。不少人都是来了美国就不走,很少人会从美国回大陆…
安娜:黄先生对不起,您的时间已经到了。对于刚才黄先生讲的,各位有什么评论吗?
李天笑:黄先生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我在中国城上班,有时候中午到中国餐馆吃饭,碰到从大陆来的代表团,有些是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大陆官员,就聊起一个问题,就是自由。
我说,你们在美国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他们不讲,然后我就说是“自由”,我就跟他们举了很多理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说话可以敞开的说,他们后来都不讲。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就像刚才黄先生所讲,到美国来团圆,而不会到中国去团圆,就是美国这个地方比中国更自由。共产党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你要是要想自由的话,那不但没有得到自由,很可能到监狱里边去自由。
安娜:那刚才这两位观众都谈到了,一位就是说你不能用金子上的那块锈和铁上的一个金点儿去相比,你要整体的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我们有很多的记者在采访中国大陆的情况,尤其是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层有很多很多各种冤屈啊,他们在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感到催人泪下!我就想到像现在中国这种情况,这种大规模的风起云涌的、民间的这种抗议活动,一波接一波,规模越来越大。那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它对中共的冲击有多大?
凌锋:我想这个冲击现在还不是很大。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跟当年陈胜、吴广是不一样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始皇暴政就结束了。现在交通也发达,资讯也很快,哪一个地方起来造反,那很快就给你镇压了!现在中国一年大概有七万多起这种造反的事件,但是因为共产党武力也很强大,调动也很快,所以一般都不能够成功的。
但是问题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腐烂,恐怕是最后垮台的因素,共产党已经没有什么理念了,就是利益集团的争夺。所以实际上不论开个什么会,比如说这个中央全会,实际上就是“利益分配”,各个利益集团能不能分配到好的,所以要妥协的。既然大家贪欲都很大,都要抢这个利益;所以最后我自己觉得共产党垮台,可能是因为自己内部争夺利益、摆不平,如果自己内部摆不平,内斗的话,那老百姓一起来,大概它就会垮台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退党”、“退团”、“退队”,也就是本身已经看不惯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最后共产党是因为自己的腐烂而倒台。
安娜:陈先生,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给您提了,有一个大陆的访民给我们电视台打电话,我们记者问他:“你觉得上访有用吗?”他说:“我觉得没用。”我们记者又问他:“那你干么还要去上访?”他说:“我就要跟他们闹一闹,让他们知道。”然后我们记者问他:“那您给我们一个海外的中文媒体打电话,您认为我们能帮你们做什么吗?”他说:“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声音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能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多人会真正了解大陆的情况。刚才你也提到了像大陆的退党、上访,各个方面的情况,您认为像这样的冲击,对中共来说,它还能坚持多久?
陈奎德:当然具体的说哪一天?多少年?恐怕很难预测,历史上要做这种预测是比较愚蠢的做法。但是我想,有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很清楚的:我也同意刚才凌锋先生说的,一个是“亡共在共”;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共的维持统治的方式,越来越注意从前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学。这些国家是怎么垮台的,它都仔细研究:喔!这个地方有个漏洞,赶快给它补掉;那个地方它们当时的政策有什么问题,我赶快把它修正一下,补一个漏洞。
是,它这个补是可以延续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漏洞是层出不穷的,这个社会每一天都在制造千百万个漏洞,去年是六万多起群体性事件,今年是七万多起,明年八万多起!它这个漏洞就像大坝的堤一样,它有很多洞,它现在还有人手可以随时去补这个漏洞,使这个大坝的堤不至于坍塌;但是到了一万个、七万个、七十万个、七百万个漏洞,它人手完全来不及补,或者它没有力量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大崩溃,而且那个洞一垮起来是完全是天崩地裂,一次性的,就是全部倒。
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国家垮台都是这样,先前看不到任何的迹象,或者所有的专家都没有预测到。苏联,这么大一个帝国,可以和美国争霸的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垮塌一下,一、两年之内就倒下了;东欧这些国家更不用说了。
所以像这种国家,它把所有的矛盾都包起来、捂起来、或填起来漏洞,平常看不见,但到了它拦不住所有的矛盾,总崩溃、总暴发的时候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它比所有其它专制政权,都由更强的手腕来堵漏洞或补坍台的、要垮的因素;但一旦它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坍塌起来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不要看目前我们看不到一些情况,一旦发生的话,应该是非常的害怕的。
凌锋:也许是银行的漏洞啊,也许是卫生方面的漏洞啊,再来一个什么SARS,搞得大家…,这个东西谁也无法知道,但是它们自己内部会出问题。
安娜:我们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纽约的林先生,林先生您请讲。林先生您在线上吗?那我们再接下一位明州的马女士。
马女士:我在国内的朋友想问一下,如果对胡锦涛的希望破灭之后呢,中国未来变革的主导力量,要来自哪里?
安娜:谢谢马女士。你们哪位回答这个问题?
凌锋:我看这个主导力量,主要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变革的前景,我觉得也是相当艰钜的。比如说共产党政权倒台以后,起来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势力,这些势力怎么样能够团结,这是比较困难;因为共产党统治中国几十年了,道德沦落、人的素质降低,所以未来前景的确是不是怎么乐观。
好的方面来看,我觉得现在宗教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发展,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如果法轮功也算是一个宗教的话,那种真善忍,现在是也有不少人从那里面寻找精神寄讬。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垮掉以后,虽然前进的道路是相当艰钜的,但是我想只要我们人的良心还在,我们相信一些宗教、导人向善的,我想中国这个社会还是会慢慢的重新建立的。
如果说一个大的中国要建立比较困难的话,那不如一个省一个省的,或是一个县一个县的,一个个把自己搞好,那么整个国家当然也会慢慢走向正轨。我是这样看的。
安娜: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乱世出英雄”,陈先生是网络杂志《观察》的总编,您一定知道很多这样的英雄吧!
陈奎德:国内当然是有很多,包括各个阶层的人,知识界的人、民间的工农大众、包括企业家,有些很有心的企业家,各个阶层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局面是不可能久的。
很多人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很好,你想想看,这样一个国家,它完全和全世界的主流体系,和它周围的国家,特别是全世界最主要力量的国家,是格格不入的一个制度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体系,所谓共产国家,它还可能维持多久?不可能维持多久的!大家都在找出路!
所以,所有最高领导人几乎子女都是在海外,他们都慢慢的把财产、把子女、把家属逐渐地转移去了,就是大厦将倾、大船将破的局面。虽然表面上他们嘴巴说得很硬,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私下的行动,都是在准备这个最后的大崩溃。但是这个大崩溃,如果是真正的突然一个社会这样大崩溃,确实是会对老百姓会造成很大的危机。
所以各个组织能够发挥自己组织自主的力量,包括企业、包括知识界、包括工农民,预先就有些组织性的网络出现、存在,然后大家有些连系,虽然中共不准人民有组织,但是有些互相的连系存在,那么到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国际社会也出把力的话,我想逐渐的还是会渡过这比较困难的阶段,逐渐的社会重建、国家重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安娜:天笑有什么高见?
李天笑:我们看到在一个旧的制度、一个腐朽的制度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新的力量往往已经露出了盟芽。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今年发生《超级女声》的大规模演出,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民主前的一个操练。从这当中显示出中国的民众通过手机选举这种方式显示他的智慧、他这种操作的能力、和这种娴熟的方式,都为将来的民主制度做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那么从基层来看,今年太石村的选举,实际上农民,最朴实的农民,文化程度可能很低,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选出了、罢免了他们党的基层领导人。所以说,这两方面都显示出了中国的盟芽都是已经在兴起。
另外一方面来看,去年年底《九评》发表,《九评》不但是文章,更是一种动员力。这种动员力在于什么?他深深在批判共产党,系统的批判共产党的理论的同时,揭露它实质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中国重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比方说,《九评》中有一评就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道德怎么复苏。实际上这个如果在民心当中、在老百姓当中,逐渐逐渐地形成一股道德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将来自然会在中国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座的这些人,将来中国很多有人才的人都会出来,只要他们是有能力、有道德的、能够管好这个国家;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非常有朝气的这种局面。
安娜:我们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马里兰州的张先生。
张先生:中国现代的发展,这个中国热,跟过去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很相像的,所以它表现出很多乱象,但是你看西方世界它照样是走过来了。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资本原始积累,付出的这么个代价、这么个过程。
那么和它相关的就是关于中共撒谎的问题,中共撒谎是大家都有共识的,但是谎言并不一定都有害。有时候谎言如果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像神六上天啊、演一个完美的中国制造啊,它能够凝聚民族力,能够把问题暂时抛下,能够使民族很快的上升。古代还有个曹操说“望梅止渴”,它就是说一个谎言,可以达到一个最后最好的目标。我觉得我们现在看问题应该从更全面、更深刻的角度去看中国现代的问题。
安娜: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中共的撒谎,它的谎言他为认为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
陈奎德:当然很多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场合下都说过谎言,很多政治家是这样。但是中共这个谎言它不是一般的谎言,它是系统性的谎言。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谎言是可能在某些暂时的情况下、一定的时空下,产生某种凝聚力;但是这个凝聚力造成的效果,恐怕谎言一旦戳穿,它的破坏性比凝聚起来的东西大得不知道多少。
因为谎言一旦被戳穿,整个社会人们的信任全部丧失掉了;整个社会信任丧失掉,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一个精神系统来支撑,那么有什么权威、有什么信仰能支撑这个社会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谎言这个东西用来治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一定是将来会造成重大的…例如共产党国家大家知道,它可能一段时间是用谎言来麻痹群众,作为愚民政策,是使得老百姓曾经信服它,但是最后像苏联、东欧,包括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家对它那一套完全不相信了以后,产生了整个社会重大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它现在是无药可救,而且整个人都坏掉了。所以这个情况,对谎言一时造成的某种效果,我看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安娜:我们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洛杉矶的李先生,您请讲。
李先生:刚才有一位先生说中国和美国一比,GDP相差三十多倍。但是我看报纸大概一个月以前,有一个美国人过去是宋美龄的朋友,他很小的时候就住在她对面,所以很熟她;他曾经担任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时的英文翻译,所以说明这个人对中国很了解。他是在上海市出生的。他说只要十五年,中国大陆就赶上美国了;那你们说美国和中国相差那么远,那他这讲话就错了?请问你对这看法怎么看呢?我认为不能看问题老是对它有成见,就拼命的诋毁它,这是不对的。
安娜:好,谢谢李先生!哪位(回答)?
李天笑: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发展是相对的,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不是说美国停在这儿,中国一直发展要赶上。现在美国人均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四万美元,中国是一千二百美元,这是它自己讲的,那么就相差三十三倍。
那么这种差距在今后是拉大或是缩小?从过去的历史来推断的话,现在实际上中国不可能再上涨,为什么?我已经讲过了,中国用的能源,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整个世界所能承担的负荷,中国现在到处找石油,如果把世界的这些能源都给中国用,中国也赶不上去。
另外,中国现在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财产,不是用到人民的生活,继续扩大到生产里边去,而是用到了大量的出逃。就是国内大量的帐面上的资金,每年有四、五百亿美元的资金出逃。最近我们看到了有四十二个银行的行长、分行长外逃。中国现在在国外定居的官员有一百二十万,其中十五万,十几万现在已经入了籍了。
为什么外逃呢?就是说他把财产拿出去以后,他不想再回来了,那么这个财产就不能够回到中国再生产,你怎么能赶的上呢?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所谓的市场经济。
另外坏帐,现在国际公认的,大概达到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这么大的银行坏帐。实际上银行是亏空,拿不出来钱的,钱都投到房地产里面去了。房地产又是谁控制的呢?跟官有关的这些人圈地,需要房地产的投资。这样的话,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处于一种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机制下,你怎么跟美国来比呢?怎么能够追的上去呢?我不知道刚才那位英文翻译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得到的资料?可能跟中国的官员接触多了以后,听得多了,从那边受到的影响吧!
安娜: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陈奎德:他说的所谓经济体总量,我们且不说他算得很错。中国是十三亿人,如果是和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去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当然比它大。但是你愿意生活在哪种国家?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美金?和一个人均收入有一万多美金或两万多美金?
这不是一个所谓经济的算法,怎么能够这样算呢?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完全相差很大很大的国家,以经济总量来算,有这种算法吗?这种算法对每个个人、国民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算法毫无意义。
你把所有亚洲国家的经济加起来比美国还要大,有什么意义?你如果把亚洲所有的国家都算成一个国家,或者算成一个共同体,和美国比,我们全部共同体的产值比你还高。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的算法!且不说他这个算法还有很多错的,就是总经济体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安娜:我想有很多的西方人去中国主要去大城市旅游或观光,他看的的确都是高楼大厦很漂亮的,可能农村的情况他们不太清楚。不知凌锋先生对这位先生的说法怎么看?
凌锋:这位先生前面还有一位先生提到原始积累的问题,说中国和西方国家以前的原始积累好像差不多的,我想原始积累的手段可能差不多,甚至于手段更加残酷。西方国家原始积累主要是比如说开煤矿,剥削是很厉害的;但中国的原始积累很特别的,什么东西呢?很多女人都是靠自己的肉体来自己原始积累。
但是西方国家原始积累赚钱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拿来再投资,所以经济发展就很快;中国的原始积累,一些官僚资本家钱赚了以后,他不是拿来再投资,他拿到外国去了。明明是资本家,钱赚了以后,他又怕将来给那些官员抢去了,就拼命的消耗、拼命的过着奢侈的生活,什么月饼几万块钱、吃菜上面要包黄金,就这样子莫明其妙地消耗掉。所以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不是那么样的乐观。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最廉价的劳动力来制造产品,来出口,但是消耗是很严重的。我这一份资料是去年的二月份的《半月谈》所出的一个杂志,它里面就讲到中国生产GDP每生产一块钱,消耗能源是全世界消耗能源平均的三倍,是日本的十三倍。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里有提到,五年规划里面中国的能源消耗要节约百分之二十,但能不能做到我并不乐观。因为中国主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本来就是浪费最厉害,因为那个管理肯定不好的,里面的工人、工作人员都想:这国家的,跟我没什么关系。这肯定是乱来的,所以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那么乐观。
安娜:说到国营企业,我想到前一段我碰到一位中国五百强大企业的副总,他跟我说:国营企业亏损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中央要让国营企业存在呢?他就让我猜两个字,他说“腐败”!然后他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腐败呢?是为了“亏损”!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
安娜:下面我们再接一位纽约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您请讲!
郑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共产党垮台的话,中国将何去何从?
安娜:好,谢谢郑先生,谢谢。他的问题是说,如果中共真的垮台了,中国将何去何从?
陈奎德:中国何去何从?走向世界大家庭呗!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当然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中共所谓垮台,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慢性的,不一定像苏联、东欧这样,也许是一个比较慢性的过程,一个非常痛苦地、挣扎地阶段,或者是有一段就是说党政机器比较混乱,然后逐渐在民间出现新力量。
但是从苏联、东欧的经验,有一点我想恐怕是一致的,就是说开始一段时间恐怕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说过去有一定权力的人或者有一定财富的人,还是会在社会上起相当的作用。我们大家注意到,包括苏联、东欧它们崩溃以后,实际上有一段时间还是过去那些在社会上执掌了某种不管是财富或者权力的人也好,在一段时间他还会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组织政党也好,搞企业也好,所以会有一段非常混乱不清的阶段,但是不管怎么说,民间的力量它一定会起来。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刚刚陈先生也谈到,宗教的力量非常重要,中国的基督教也好、法轮功等准宗教也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好,它实际上在社会逐渐伸展起某种真正的、健康性的力量。
就像古罗马后期,古罗马实际上当时也很繁荣啊,但是很腐败、很奢侈,然后基督去传教,基督教像野火一样在民间燃烧,虽然被国家继续镇压,但是逐渐传播,然后他对后来欧洲国家各个民主国家的建立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后来这个宗教成为国家的主体、精神性的力量,甚至在有些国家成了国教。所以这样一种逐渐从泥土底下、从草根底下逐渐建立起来,才能比较持久,虽然有一段过渡时期,还是有权力的人会掌握一定的优势,但是那一段时间只是个过渡时期,我们不能很准确地预测一定是哪个党派占优势,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健康性、草根性的力量逐渐来成长起来,逐渐重建这个社会、重建这个国家。
安娜:那我们现在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纽约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讲。
刘先生:你好!我刚才听凌锋先生说,假如共产党倒台以后会有什么宗教方式的,比如法轮功啦来领导中国,这个事情要一个一个省一个一个市的来,我想这个讲法太肤浅、太简单,我觉得应该借鉴这个台湾的方式,就是培养一个大的政党,就是在野党,逐渐壮大起来有这个实力去给共产党送终。有这个领导能力去领导一个国家,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你这种说法吧,不像一个政治家所说出来的话,是不是?
陈奎德:你容我说两句好不好。
刘先生:你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谈这些,中国一千多个县市,要用这样的方式的话,这不可能的事!我觉得你这个看法太肤浅,我认为要借鉴台湾的经验,要组织在野党。
主持人安娜:好,刘先生。您们哪位回答这位先生?
凌锋:我想这个问题啊,刚才我回答的意思是说,做为一个社会的力量,肯定有领导人嘛!有一个领导把这个社会力量带动起来。这位先生讲得也很好,要培养一个政党,问题是共产党不让你培养,你稍微几个人成一个组织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不是说老百姓不想组党,是共产党不让你组党。
所以这样子的话,再来如果即使出现混乱,我觉得负最大责任的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让反对党存在?让你有一个竞争!万一倒台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可以顶上来,是共产党不让做。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力量,人心基本上是向善的,那么这样子就可以防止混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最近一阵,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份子、一些专业人士,共产党花了很多金钱去收买他们,让他们过好生活,所以他们很多都为共产党讲话。
但是我也看到最近一阵,很多律师都出来了,帮那些弱势族群讲话,包括这个太石村大概有几十个律师组织一个团,来帮他们讲话。还有一个郭飞熊律师,还有唐荆陵,还有一个郭艳。那郭飞熊律师被他们抓起来,所以这些就像台湾当年为美丽岛事件辩护的律师陈水扁,后来都成了领导人。
所以我想中国这些专业人士,除了律师,还有我们也看到像艾晓明,是中山大学的教授;还有东北的一个卢雪松。他们都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下,这些专业人士、知识份子都站出来帮弱势族群讲话,我想他们这些以后在民众当中、草根当中,他们会有很大的威望。那再来出现乱局的话,他们就出来,我想他们就会有一定的群众来支持他们。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慢慢的组成一种团体,甚至以后会有一个政党,我想这样子将来在中国政治转折当中,我想他们是会发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
安娜:刚刚陈先生谈的这个比如说像一些有信仰的人,像基督教,还有“准宗教”像您刚才说这个法轮功学员,您给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有一些良性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
陈奎德:我讲的是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政党是一定会起来的,这是人性,这是政治的基本规律。就像台湾一样。刚才我不想说详细的过程,我专门写书和文章,谈台湾是怎么样转化的,他有精英的这条路,通过办杂志来凝聚政党,通过基层选举来凝聚所谓的党外,最后成了民进党。
还有通过基层选举来达到,一个是草根、一个是精英办杂志的凝聚,这是藉着互相的共识,这样的两条路逐渐凝聚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仔细要讲详细的过程,我是指的包括信仰性的、宗教性的、健康性的,就是说有道德性的力量,在历史的长远的过程中间会起一个健康性的作用。
这是一个电击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从长远的政治发展来看,对政治发展的方向是有好处的,至于解除党禁、报禁以后,根据政治规律一定会出现多党竞争一定会出现多种舆论竞争这个局面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就是有一段乱局而已。
李天笑:刚才这位先生讲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刚刚陈先生他是讲了两个要点,一个是讲公民社会,就是说公民社会就是国家的权益收缩以后,各种的团体组织,他的权益、自由度增大,这个就是民主政治,政党竞争的最基本要素,没有这点不可能产生。
第二个、他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的力量,你这个团体的竞选人出来,你的领导人出来,要竞选政治权益的话,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进行竞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来说,现在的权利分赃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用台湾的这个方法,实际上这个民主政治是从内部逐渐地自然形成,而不是外来注入的,共产党就是外来注入的西来幽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建党,它注定是要失败的,不为中国的环境所接受的,我觉得刚才那个凌锋先生和陈先生讲的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刚才那位先生可能是从另外角度看这个问题。
安娜:从刚才你们几位所说的这些情况,的确现在在大陆的状况,中共真是越走越往末路上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海内外,我们看到《大纪元》网站上那个退党网站已经有将近500万人退党,那还不用说有很多人他不会上网,他没办法到网上去“退党”,可能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我们看到胡锦涛对此所做的对策是什么呢,是“保先运动”,扩大招收党员,那你认为他这样做能够挽救中共吗?
李天笑:他如果能够挽救中共的话,那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就不会存在,根本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先进过,它根本谈不上保先这个问题,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落后的制度,一种野蛮封建的制度,方式上它是一种流氓、暴力这种方式来夺取政权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掠夺性的,对中国人来说是种掠夺性,长期以来它用一种依附在中国人身上,不断掠夺,吸取中国人的血汗,来壮大自己这么一种特质。
所以说从来就不是先进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几种方式,曾经有人分析共产党会垮台解体,一种是外来的,从外来的军事力量,对中国采取封锁包围,但是呢如果不采取武力的根除,那是达不到的,这是不行。第二种是通过经济的方式,通过发展中国的经济,注入资金,从和平演变的方式,自然生起一个中产阶级,这种方式目前到现在来看也不行,用经济的方式也不行。
现在是什么方式,通过“退党”的方式,它是从内部,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这内在的力量是从两方面,一个是从党内出来的;第二个是从人的内心一种觉醒,这个力量非常大,而且使共产党解体于无形之中,不会给中国造成动乱或者什么,它是一种非常平稳的一种过渡,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从这方面去理解就可以了。
安娜:那陈先生有什么高见吗?
陈奎德:我想刚才李先生说的都是很对,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很硬的方式不跟你合作,我不跟你玩了嘛,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式的创造了一种不合作的运动,和当局不合作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类似像甘地他当年和英国殖民地当局不合作的运动一样,他是处于一种文明而且是非对抗性的、非流血似的、非暴力式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决你的政权的正当性,否决你的合法性,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恐怕是相当有启发性意义,对历史来说,对一般人心来说都会有很大的鼓舞性力量。
安娜:刚才陈先生谈到有很多中共的高官,他们都把大量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家属转移海外,你认为他们这些作为会不会加速这个中共的灭亡?
凌锋:我想这也是和中央不合作的一个棋子,现在不合作不管是上海,上海是不合作,所以胡锦涛要换人,现在连军队也不合作,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11日五中全会闭幕,12日一方面是神六上天,一方面胡锦涛突然跑到南京军区视察,有这样紧急吗?会开完立刻到军区去,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安娜: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希望下次节目还能见到各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见。
——————–
“無論是維護中共政權的人還是希望中共倒台的人,其實都不否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政權之腐敗與不公,早已大大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政權。
維護中共政權的人之所以維護它,當然首先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同時,他們一般也相信,中共政權不可動搖,因為一旦動搖,則傾巢之下,沒有完卵,因此,不論中共多腐敗,多數人也不會允許它垮臺。希望中共倒台的人,則認為如此腐敗的政權一日不去,中國就沒有希望。”
——《汉源民变加剧中共危机 胡温仍未放弃幻想》 梁京, 11/16/2004
有人说,历史在不断地重演,还记得1961年8月13日凌晨2时,一道道耀眼的探照灯刺破夜空,宣告了柏林市28年东西分隔的开始。星期天,当柏林人一觉醒来时,发现一道40公里长的带刺铁丝网沿着苏联占领区界限被匆匆布下。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发布命令,用铁丝网封锁西柏林,后改为混凝土墙,建成举世瞩目的"柏林墙",切断了东西柏林间的自由往来。
事实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爱国,因为他们敢于分担政治的命运,他们耻于接受一种不自由的统治。
今天的中共统治危机重重,刚刚闭幕的五中全会不出很多观察人士的意料,还是旧瓶旧酒,不见有政改的迹象,那么在五中全会之后?这些重重危机将如何发展?如何影响到十数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就此热点问题,新唐人热点互动继续追踪探讨这个话题,诚邀您参与热线互动,一起关注这个时局问题。
美东时间周五10月14日晚9点,敬请锁定新唐人热线直播。
纽约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免费长途热线: (866)NTDTV-OK 866-683-8865